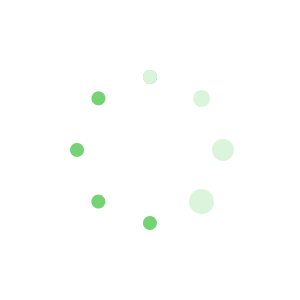摘要:从现象学的视角探讨儿童“表演”行为,分析儿童“表演”行为背后的成长期待,即成人对儿童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儿童对自己的期待,从而影响儿童自身的行为表现。通过呈现典型案例,倾听儿童内心独白,关注儿童在“表演”行为中的自我寻求。再转向成人角度,反思发现成人易忽视儿童“表演”的行为意义,过度外在化评价标准以及偏向满足“推断的需要”,人为遮蔽了儿童“表演”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在此基础上,探析儿童作为“表演”行为之意义主体的教育学意蕴,以幸福目的论为起点,从关注儿童行为的因果关系转向意义关系,从过度外在化评价标准转向理解为主的标准,有利于成人真正深入儿童内心世界。
关键词:儿童“表演”行为 自我追寻 意义主体 现象学视角
引用格式:周晴.儿童“表演”行为意义阐释的现象学透视[J].教学与管理,2022(18):50-53.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表演是作为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即只要有自我、角色和他人在场,在某种程度上便会发生表演行为[1]。表演是个体通过对角色的塑造而达到使得他人确信的目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呈现。儿童虽然年纪尚小,但作为独立个体,其日常生活中的“表演”行为并不少见,在不同情境中儿童通过对角色的塑造呈现出不同的自我。儿童的“表演”行为体验本身是什么?儿童的“表演”又意味着什么?成人是否又真正理解儿童的真实意图呢?本文尝试从现象学视角理解儿童“表演”行为背后的意义,并探析兒童作为“表演”行为之意义主体的教育学意蕴,为当下教育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儿童“表演”行为的案例呈现
现象学研究的是现象的本质,即使某“事物”成为某事物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它就不成其为该事物[2]。通过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对于日常生活体验的意义更为深刻的理解。为探寻儿童“表演”行为背后的真实意义,笔者选择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来进行现象学分析。
安安是一位六年级的女孩,之前的学习成绩均是班级前三名。在她最近几次的考试中,成绩却突然下降了二十多个名次。在和我的聊天中,安安的妈妈这样说到,“我们这段时间的教育方式没有什么变化啊,还是和之前一样,我每天下班回来一边做饭一边监督她做作业,晚上再检查作业完成情况。她爸爸平时上班挺忙的,主要也就是周末辅导孩子。这孩子最近在家也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有时候还主动要求延长做作业时间。看她这样熬夜也挺辛苦的,可这成绩怎么不进步反而退步了呢?昨天问她也不说,孩子爸爸就说了她几句……”
安安的爸爸则在一旁和安安的弟弟看动画片,并没有加入这次聊天。当我走进安安的房间时,她正在一边用手遮挡着作业,一边使用彩笔涂色。
“你在干嘛呀,安安?”
“嘘,不要告诉我爸妈,等我完成这幅佳作马上就写作业。”
之后在我和安安的交谈中,她说她最近在班上创业,成功当起了“老板”——卖画,并以一张五块钱的价格,收获了一笔不菲的收入。
“学校同学都夸我呢,我还认识了好多好朋友,她们一下课就来找我玩,还让我教他们画画呢”,安安一脸骄傲地和我说。
安安从小非常喜欢画漫画,之前跟着专业老师系统学过,并获得市级奖项。后来到四年级时,父母以耽误学习为由拒绝。但她依然每天偷偷在课堂上画画,回家后把画和卖画所得买的零食、玩具偷偷藏起来。当我和安安聊到她的家人时,她低下头,双手在不停的揉搓,声音也逐渐变小了。她觉得弟弟出生后,父母没有像以前那样关心自己了。她觉得父母最近都没有抱过自己了,反而经常把弟弟抱在怀里。如果她自己在家再不好好表现,好好看书,乖乖听话,父母就会对自己更失望,更不喜欢自己了。
在现代汉语中,“表演”一词具有朝向外的意向性;目的是要向他人显示、传达或投射某种信息;所使用的基本媒体是语言和行为之类的符号。关于儿童“表演”行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本文认为儿童“表演”行为是指儿童围绕周围的个体为“意向对象”,与其建立范围有限的意向关系[3]。即借助“表演”行为呈现他有意表达的印象,以影响其他人看待他的方式。也就是说,“表演”是儿童反映其自我感受和生活体验的一种方式。案例中,安安通过“表演”试图让父母相信自己是“好孩子”,她的父母也将教育孩子的重点放在成绩下降的事实和“听话”的表面行为上,并未和孩子进行更进一步的交流,并给予关心,这使他们忽视了探寻成绩下降,却在家积极表现背后的真实原因。而在我与安安的私下交流中,安安则回归了相对真实的自我。也就是说,缺少父母的在场和“好孩子”角色的束缚,儿童更有可能呈现相对较为真实的自我形象。
二、儿童在“表演”行为中的自我寻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不断地自我寻求而成为自己[4]。相对来说,儿童的自我寻求并没有成人那般复杂,“表演”中的儿童在不同情境下所呈现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儿童寻求存在感和幸福感的一种“探索”。
1.“我”想做“你们”喜欢的好孩子
“我”的自述: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都喜欢聪明的、成绩好的孩子,我也想做你们喜欢的好孩子。考试考得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学校,老师已经批评过我了,我很难过,也不敢和你们说。我只能在家里多做一会作业,这样你们就会看到,就知道我很听话了,也知道我也想成为好孩子(自述材料来自于对安安的访谈)。
罗洛·梅曾说过,“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是根据行动本身,而是根据该行动被接受的程度来判断其行动的价值”[5]。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成人习惯将目光盯在儿童行为表现出的价值上,并非儿童行为本身,较少关心儿童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行为且时常将“好孩子”“坏孩子”挂在嘴边,用他们对儿童的期待作为标准去衡量儿童。长此以往,这种教育方式易导致儿童尤其在意成人的眼光及评价。因而,他们一旦感受到成人对自己的不满,就会通过“表演”成人想看到的表现而达到成人的期待标准。实际上,这是儿童在寻求自我的路上,以期望获得存在感的一种表达方式。
2.“我”想成为“你们”的骄傲
“我”的自述:每次儿童节晚会上,老师和家长们都夸奖那些上台表演的同学。我想让我的爸爸妈妈也听到这种话,我想成为他们的骄傲,所以我要好好学习画画,偷偷参加比赛,就像以前一样,把奖状拿回家给他们看。而且,我卖画还能赚钱,可以给爸爸妈妈减轻负担,这样妈妈就不用每天辛苦地上班了,她就有时间陪我了(自述材料来自于对安安的访谈)。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细化地分为七层,前四层被称为缺失性需求,即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的需求,产生这种需求的根本原因是其在心理或者精神上存在一定的欠缺。后三层被统称为成长性需求,即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儿童的需要层次大多集中在前五层。一方面,当儿童的内心渴求来自成人的认可时,说明此时儿童的缺失性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成人应具备必要的教育敏感性,有针对性地观察、聆听具体情境中的儿童,积极与他们进行互动,及时给予儿童反馈,满足他们的需求[6]。另一方面,儿童渴望成为父母的骄傲,这也是一种积极表达爱的方式,因为儿童与父母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渴望通过自己的默默努力带给他们骄傲与荣誉,达到他们的期待。
3.“我”想要一个拥抱
“我”的自述:我也想让爸爸妈妈抱抱我,可是爸爸总是喜欢抱弟弟,夸弟弟聪明、可爱。我也很喜欢弟弟,我也想他们看看我,我平时也会赚钱买零食给弟弟吃,带他出去玩,我也是个好姐姐啊(自述材料来自于对安安的访谈)。
麦金太尔曾指出,当我们描述行为时,需要考虑具体背景[7]。儿童为何做出“表演”行為?这对他们本身意味着什么?安安经历了从“无弟弟的存在,自己独享父母的爱”到“弟弟的出生,与他分享父母的爱”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安安通过具体行为调整自己的角色,努力做一个好姐姐,具有了一定的爱他人的能力。可是安安的爸爸却将更多的拥抱与关爱给了弟弟,忽视了安安爱的需求,当这种“爱他人”的付出和“被爱”的需求没有达到平衡时,儿童的心理便会有一种失落感。他们可能尝试以其他的方式获得他人的关注,进而来换取需要的温暖与爱。这是儿童自己的处理方式,成人不应从单维度分析儿童行为,应结合具体背景变化对儿童行为进行深度剖析。
三、成人在儿童“表演”行为中的教育反思
范梅南指出,在与儿童交往的情境中,教育者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教育。其原因在于教育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可定义的,只有不懈努力进行创造性的教育,才能为发掘教育深层意义带来希望与光明[8]。限于儿童身心发展的不成熟,在很多行为上仍然需要依靠成人的帮助。这就要求成人站在儿童立场不断地进行反思,明白儿童的“表演”行为对儿童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1.成人被儿童有意引导,忽略儿童“表演”行为的真实意义
戈夫曼认为,在“表演”行为中,不管表演者心怀何种特定目的,他的兴趣总是在于控制、引导他人应对他的行为方式。这种有意引导的作用过程是通过表达自己来影响他人正在形成的情境定义,从而给他人留下印象[9]。案例中安安在做出“主动要求延长作业时间”“在家里变得比之前更听话”等表演行为之前已经熟知父母惯用的教育方式,提前划定可控范围区域。这就导致成人被儿童有意引导逐步关注他们的“表演”行为,忽略儿童“表演”行为的真正意义所在。儿童之所以塑造“听话、积极”的角色,是因为儿童渴望获得这种角色带来的体验,即父母的关爱与认可这种精神性的满足。
2.长期扮演单一角色,过度关注外在化评价
儿童“表演”是儿童借助行为向成人或教育者表达其意识内容的表现行为。当成人看待儿童行为时,往往习惯设定外在化评价准则,而儿童在此行为表现中则关注自身的内在体验以及自我意识[10]。这与双方长期承担的角色有关,大部分成人在家庭中与儿童直接相关的角色相对比较单一,除了担任具有教育者意味的父母之外,较少同时承担其他角色。在案例中,即使安安的父母知道她的兴趣是画画,也会以耽误学习为由拒绝。这种仅以学习成绩和日常可见的乖巧作为评价儿童的标准是成人根据对于儿童理想化的期望制定的。在教育过程中,一方面,父母如果长期在孩子面前扮演单一角色,会不利于儿童多维度认识自己的父母,甚至会因为“父母”这一角色自带的权威感而拉大与孩子间的距离。另一方面,父母长期过度使用外在化的标准来评价孩子,将很有可能造成孩子在达不到父母设定的过度理想化的标准之下另寻他路来获得自己需要的体验和感受。
3.习惯程式化关怀,偏向满足“推断的需要”
内尔·诺丁斯指出,程式化的关心是以解决数学方程式的思路来分析问题,具有控制、标准和理性的色彩[11]。当儿童由问题引发“表演”行为时,成人的处理思路通常是“针对问题进行常规教育——转向关注儿童“表演”行为——缺乏持续追问,不了了之”。除此之外,成人偏向满足“推断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指由外部引起的需要,是他人强加给那些说有这种需要的人身上的需要。对儿童而言,这种需要一般是成人推想出来的,是强加给儿童的需要[12]。案例中安安的父母一开始在询问其原因无果后习惯性批评了安安,也没有进一步进行追问与关心。整个过程中,作为父母的成年人忽略儿童作为独特个体的情感和内心体验。在与我的交流中,只要我一提到“画画”她就会表露出骄傲而开心的神情;而谈到家人时,她则“低下头来,双手在不停地揉搓,声音也逐渐变小了”。可以得知安安十分渴望来自父母的关爱,以满足自己在家庭中本应获得的精神性需要。然而,成人始终无法体会到儿童非身体化的体验及其渴望关爱、害怕被忽视等情感所传递的内心需求。这种程式化的关怀甚至使得关心异化成了成人对于儿童的过度期待,带给儿童的则是按照成人期待的那样来行动。
四、儿童作为“表演”行为之意义主体的教育学意蕴
现象学是一门探究生活现象以及体验的学问。尤其在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寻上,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它试图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来描述和解释这些存在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意义[13]。儿童的“表演”行为是儿童在某一特定情境下的自我存在意义的表达。要想真正地理解儿童,体验儿童的世界,就要求教育者进行主体转换,也就是说,把教育者放在行动者的位子上,然后把教育者的意识体验跟他人的意识体验藉由观察到的相同类型的行动等同起来[14]。
1.深入儿童内心世界,从关注儿童行为的因果关系转向意义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就是对世界某些方面的感知。要想深入儿童的内心世界,需要打通“意识”这条通路。但“意识”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并不能被准确描述,成人可以通过进行现象学的反思来阐明自己的意识,儿童因受身心发展程度限制,其意识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赖成人的解释。只有说儿童说的话、想儿童之所想,从而深入儿童的内心世界,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诠释出儿童的自我意识。但仅仅进入儿童内心世界是远远不够的,成人需要理解儿童“表演”行为背后的内在意义,清晰把握儿童在思考什么,明确他在体验什么。由此进入儿童的意义世界,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15]。儿童做出任何行为的背后是自我的表达,成人不应该仅仅关注儿童行为的因果关系,还需要关注儿童行为的意义关系。无论这种行为是问题行为还是非问题行为,都是强调行为主体自身的情感体验与存在意义。两种关系的区别在于,因果关系强调外部因素对儿童的影响,意义关系则突出儿童自身对其行为的影响;前者旨在描述、说明儿童行为,后者则试图理解儿童行为。
2.转换视角与立场,从外在化评价标准转向理解为主的标准
就如格鲁梅特指出的那样,父母身份召唤我们再次回到童年,通过孩子的世界来思考问题。成人与儿童的经验世界有差别,也就是说衡量事物的标准存在差异。成人不可过度将自己的标准嫁接到儿童身上,比如对儿童成绩、能力设定过高要求。转换视角与立场,就要求成年人适当摒弃过度外在化的评价标准,转向以理解为主的评价标准。当作为父母的成年人设立过度外在化标准的同时,就意味着父母在孩子面前开始走上了权威式的父母之路。苏格拉底在《米诺》中将对话的基本结构比作友谊关系,对话双方像朋友一样在交谈,没有权威与服从,没有过度外在化的标准比照,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流和平等立场上的谈心。成人如果能够将视角从观众转为倾听者,将立场从父母转为朋友,将过度外在化评价标准转向建立在视角与立场转变基础之上的以理解为主的标准,通过感知儿童真实的生活体验和需求,及时回应儿童的正当真实需要,这对追问儿童“表演”行为的本来面目有重要作用。
3.确立幸福目的论,从“推断的需要”转向“明示的需要”
“幸福”这一目的始终是人类追求的。在成人对儿童的教育过程中,不否认其他目的存在的重要性,但就各种目的间的关系而言,“幸福”始终是处于核心地位。诺丁斯进一步指出,要理解幸福作为教育目的的真实意蕴,要将这一目的付诸实践。这里的“幸福”,一方面是指教育者要帮助儿童理解幸福观的本质是什么,并通过不断分析和实践,让儿童形成在幸福方面的可靠立场,另一方面意味教育者要调整评价观,根据幸福的实质进行评价[16]。可以看出以上的两层含义都是指向行动的。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要求教育者亲身与儿童共成长、共反思,而不是仅仅依据成人的思维方式去揣测儿童的行为意义[17]。另外,成人应以这一目的来满足儿童需求,关注儿童的存在意义。对于儿童来说,“推断的需要”是成人强加给他们的需要,是成人给予儿童过高的成长期待,它的存在是在为成人给儿童某种强制性措施提供了辩护[18]。相比较而言,那些在儿童内心产生的“明示的需要”,可以用儿童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需要才是教育者應该明确的。成人需要真正从关注儿童“推断的需要”转向注重儿童“明示的需要”来帮儿童获得幸福,因为幸福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明示的需要”和“推断的需要”之间建立一种基于持续对话的平衡[19]。
参考文献
[1][3]李政涛.教育生活中的表演—人类行为表演性的教育学考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
[2][8][13] 马克斯·范梅南.生活体验研究[M].宋广文,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3,11,14.
[4] 郑蕊,周兴国.存在感与价值感:留守儿童的自我寻求[J].基础教育,2018,15(04):29-34.
[5] 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M].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0.
[6] 马克斯·范梅南,李树英.教育的情调[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12.
[7] 麦金太尔.追求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61.
[9]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10][14][15] 周兴国.人文科学视野中的“儿童问题行为”及其实践意蕴[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39-45.
[11][12][16][19] 诺丁斯.幸福与教育[M].龙宝新,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6,9.
[17] 卓晓孟.儿童“偷窃”现象背后的认同危机及伦理关怀[J].教学与管理,2018(23):1-3.
[18] 龙宝新.教育:为了幸福的事业——论诺丁斯的幸福教育观[J].基础教育,2012,9(01):10-16+20.
[作者:周晴(1996-),女,安徽池州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
猜你喜欢 行为表演儿童 社区老年人跌倒认知和行为调查与分析上海医药(2016年20期)2016-11-09儿童玩具设计要素文艺生活·中旬刊(2016年9期)2016-11-07反腐败从正人心开始企业导报(2016年19期)2016-11-05想象力在舞蹈表演中的重要意义科学与财富(2016年28期)2016-10-14留守儿童杂文选刊(2016年7期)2016-08-02六一儿童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6年6期)2016-05-14“六·一”——我们过年啦!小学生·新读写(2006年6期)2006-06-14捏脊治疗儿童营养不良祝您健康(1990年6期)1990-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