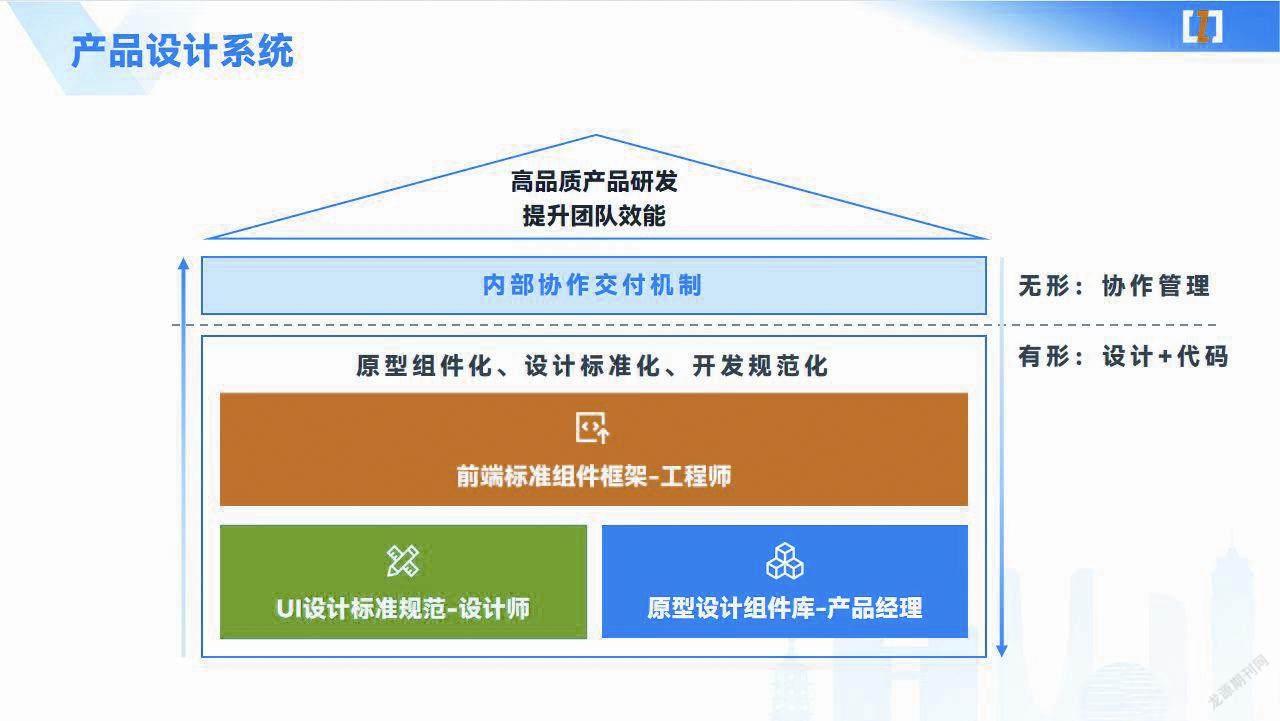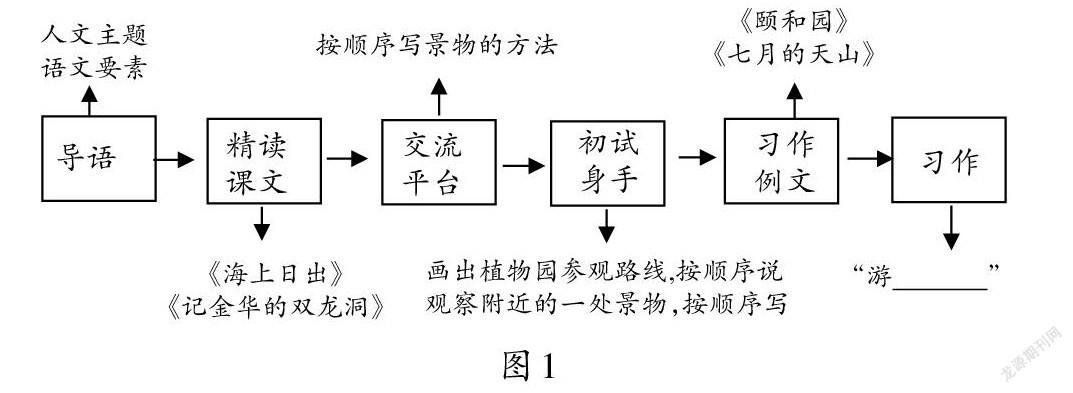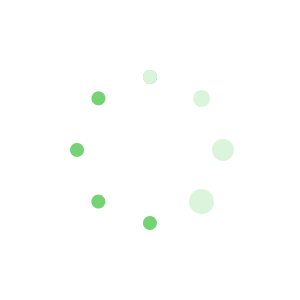赵芳芳
一
1938年,民国27年,岁在戊寅,日本侵华战机大规模轰炸广东。此时,离广州城几百里外的粤西南,有个临海的地区叫台山邑,一个小女孩在此出生。同年10月,战事升级,民国广东省政府大批机构紧急撤退,“与军事同时并进”的金融业也坚守不住,不得不分批撤离广州。
1943年,广东大旱,百万人饿死,日机更接连轰炸,重创广州,南粤大地,一片疮痍。这一年,那个小女孩的父亲,一位年轻的银行职员,在台山锦昌村家中,把女孩及她的哥哥、妹妹叫到身边,沉重地说:“国难当头,为防万一,省行不得不要搬家,分南下北上撤退……”
2015年,当年的小女孩,我的母亲,在电话里哽咽着说,那时我不到四岁,但死死记住这几句话,不清楚什么意思,只知道父亲要离家。那一年,我外公随广东省银行最后一批人员,从广州撤到廉江。廉江濒临北部湾,从版图上看,几乎處于大陆最南端。路途迢迢,风雨潇疎,外公远离妻儿,颠沛流离。也许命中注定,也许水土不适,长途跋涉到廉江不久,外公突染重疾,一病而终。千里外的台山邑,他年轻的妻子我的外婆,幼小的儿女我的妈妈及舅父小姨,天天翘首凝望。殊不知,烽烟弥漫,音信两无,亲人远隔,从此万水千山。
关于外公的过世,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妈妈说。握着电话筒,泪水奔涌,流向1943年,那个兵荒马乱的冬月。
那一年,外公三十六岁,外婆只有二十八岁。
外婆的娘家叫宝贝坑,那里有她的妈妈和四个弟弟。外婆的妈妈,我唤作阿白,阿白与外婆神貌相似,典型的广东女子,娇小,秀气,短发微卷。当然,我出生并记事时,两位老人都真的老了,我无法清晰知道他们年轻的模样。看过照片,小家碧玉。
据说,当年阿白关于女婿的人选有两个,一个家境殷实,有大屋有田地,另一个家世一般。阿白向媒婆仔细打听,了解到家境好的男子智力平庸,游手好闲。而另一位,小小年纪只身到省城广州,在洗衣店当学徒,像很多电影看到的小学徒一样,白天埋头干活,晚上秉烛读书,一个农耕子弟,咬牙苦熬,凭着努力和天赋,居然考进广东省银行事情,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乡人无不褒扬。精明的阿白毫不犹豫,即刻选定了这一位,阿白认为,吃苦耐劳,秉性聪明,这是幸福家庭的根本。从此,他成了我外公,大名伍炳光,字遇时。从舅父、妈妈的年纪推算,外婆结婚时正当碧玉年华。可以想象,郎才女貌,君情妾意,多么美好的姻缘。那个叫锦昌村的家,成为外婆一生的负累和责任。
外公在广州工作,省城跟台山锦昌村之间,隔着大小五条河流,每回一次家,都要辗转水路车路,乘船乘车加上步行,至少两天时间。这天,又到了休息回家的日子,外公早早起来,提着两大包东西直奔车站。这次,他带着一件香云纱褂子,准备送给新婚妻子。他喜欢香云纱清亮爽滑,喜欢香云纱穿在自己爱的女孩身上,喜欢女孩穿着香云纱柔弱如水的样子。积攒很久,终于买到。外公的心,早飞到几百里外的锦昌村。
锦昌村不大,村头大声喊,村尾隐约可听,外婆的家在村头,隔着一个水井,一脉小溪,曲曲弯弯的小路尽头,就是通向县城的公路,村里人都叫车路。我的幼年时光,就在这里度过,一草一木,瓢碗凳盏,都非常熟悉。水井台,围着水井砌起一圈小围栏,必去玩耍之地,外婆怕我掉下井,每次都大声喊“唔准行埋水井(不准靠近水井)”。如果妈妈从外面的车路走来,外婆又说,“阿芳,企到井台望下到未(站到井台望下到了没有)”。于是,水井周围,童年的我,留下许多踪迹。手扶着台圈边,伸头到水井看水面倒影;围着水井玩跳格子;有人打水,抢着放水桶,只为听到桶底接触水面的一声“啪”……后来听说,水井有一百多年历史,当年玩耍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也许在某个时刻,我的,就和先辈的足迹重叠在一起。当年,外婆一担水桶,外公扶着担杆,你挑水,我淋菜,这样的日子肯定是有的。水井有情,必记得外婆外公琴瑟调和的身影,记得重逢的欢悦,分离的凄怅。而这里,几十年来,也成了我情感寄寓所在地。
三十岁的外婆,正当美眷如花。
外公过世后,广东省银行没忘记他身后的妻儿,抚恤金发到村里。但母亲说,外婆既没见过抚恤文书,也不知道金额。按理,外婆知书识墨,办理这样一桩大事,理应由她出面,可是没有。七八十年前的广东乡下,世俗人情如何,由此透出端倪。外婆只被告知,每月到县城一间米铺,签名画押领取二十斤大米(谷)。
外婆没有缠足,但走几十里,从锦昌村走到县城米铺,再肩挑二十斤(也许还有其他),再一步步走回锦昌村,对一个弱小女子,足够艰难,何况,肩膀上压着,她亲爱的丈夫用性命换来的救命粮食。这般沉重,年轻的外婆怎么承受?这样的苦难,怎么逾越呢。每每想到这种情景,我的心犹如刀剜锥刺。外婆告诉妈妈,从踏出米铺开始,泪水就淌下,淌不尽的悲惨凄凉,流不完的思念怀想,一路走,一路哭,寸肠欲断,翻江倒海。泪水伴着风尘,当转入锦昌村前的小路时,隐隐约约,外婆似乎听到孩子们说话,想起家里年高体弱的公公,心中一凛,赶紧擦干泪水,加快脚步。走进家门时,已换上另一副面貌,大声说,今晚有饱饭吃了。
二
一个人的坚强并非与生俱来,千般痛苦,万般砥砺,才会长出硬壳,护着伤透的心。那些漫长愁苦的岁月里,外婆所受的种种磨难、屈辱,我都无法想象。母亲一篇回忆文章这么写:
一瘫痪的邻居老妇偷偷对我妈说,我粗言骂她。向来管教儿女严格的母亲火从心起,恼怒之下,拿出孖鞭子,把我叫到近前。
快快说来,你今天做错什么?没有。
岂料那老妇从旁怂恿:“不打会招吗?要用力打!”
还不认错?母亲厉声说。
我没错,要我招认什么?孤立无援的我斩钉截铁。
你还嘴硬?硬得过鞭子吗?妈的话音未落就一下抽打在我小腿上,两条淤血的鞭痕红彤彤,我痛得眼泪汪汪,哭喊着:哎哟妈呀,我有什么错?错在哪里?
你为何这么不知情义?口口声声老太太的骂谁?
我顿时恍然大悟,又气又怒,恸哭着据理抗辩:谁生造是非说骂人?我是背书!不信您就听吧:老太太放羊去吃草,羊到田里去吃菜。老太太叫羊回来,羊说我不回来,老太太……然后大声说:课文就这98个字,没有错也没有漏,我记得清清楚楚,哪一句骂人啦?没有呀!
那老妇听了哑口无言,我妈听着知道错怪我了,但严厉的她却要我马上停止号哭。
外婆的刚烈与严厉,不仅仅对母亲。记得四五岁时,一天,外婆突然说,放在抽屉里的两块钱不见了,但没有看见外人进屋。“是不是你拿的?”她厉声质问。小时候的我,常常跟村里小孩玩,野得上山下地,会爬树摘花稔果,也会下水摸泥鳅,但外婆管教严,偷钱这种小动作是不会做,也不敢做的。可是,这次外婆黑着脸,问不出结果,居然拿烧火钳子夹我的手指。是不是你拿的?是不是?我害怕极了,放声哭。越哭,钳子夹得越紧,疼痛从指头传到心里,巨大的恐惧笼罩,只想立刻逃离。于是,在外婆连声追问下,胡乱承认了。可是,外婆马上又问,钱给了谁?这么多钱藏在哪里?可怜的我只好继续编,“给了国梁哥”。国梁哥是放牛仔,经常从野外带回烩番薯,篱笆上只要长出喇叭花,他就会摘下来给我。
几十年过去,最后结局怎样,已经淡忘。很长一段时间不理解,外婆为何这么狠心?也从不敢告诉妈妈,小时不敢,成年后还是不敢,怕妈妈伤心,怕她误会外婆。对当年无知赖上国梁哥,心存愧疚,甚至回到那个小村子,总希望遇到国梁哥,当面向他道歉。
理解外婆,心疼外婆,是慢慢知道她的故事后。一个三十岁守寡的年轻女子,没有坚硬的心胸,倔强的品性,决绝的所为,又怎能于族人的欺凌和生活的窘迫中,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成年后,尤其在外婆去世后,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外婆被同村婶婆辱骂的情景,心酸难眠。所幸,母亲兄妹三人很争气,都上学读书。母亲感叹,没有外婆的开明,就没有她的今天。当年母亲上学,村人闲言杂语,认为“女大面向出,穷人弃学富家礼?”更有族人向外婆施压,不让母亲上学。外婆虽然孀居乡野,但懂人情明事理,又可能,聪慧的丈夫所给予的熏陶,自小接受的家塾教育开启了蒙昧的心胸,面对各种毒舌,不为所动,宁愿借米赊粮,也要供母亲继续读书。六年制的小学,母亲只读了三年半,却以全乡第一名,唯一的一个考上全县最高学府台山第一中学。兄妹几人中学、中专、大专先后毕业,都当过老师。五六十年代,这样的家庭不多,在锦昌村,更是独一无二。
我想,这一切外公是知道的,他的照片,一直摆放在外婆的梳妆台上。梳妆台,其实就是一张老木案台,板面粗糙,色泽黑亮,台面除了外公的照片,什么也没有。这照片,从我记事开始就在那里,一直到外婆过世,还在那里。我对外公的最初印象,就是这张照片,白短褂,灰色西裤,左手收在背后,英俊帅气。小时候,偶尔会对着照片发呆,觉得外公是古代人。每逢什么年节,外婆就在照片前放个小香座,燃一炷香。我不知什么意思,每当这个时候,外婆都沉着脸,所以不敢多嘴。每次看着烟雾冉冉而起,心里似有东西慢慢下沉。多少年后,我终于明白,外婆以一种虔诚的方式,与外公对话。既然不能执手偕老,就把你摆在眼前,供在心里,让你看着一家子,看着孩子们吵吵闹闹,从总角到成年,看着我忙忙碌碌,从青丝走向白头;看着时光如何暗了又亮,短了又长,长长短短的日子,叠加为锦昌村这一家的苦和甜。
一个人的一生,让另一个人的一生来安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爱情吧?而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故事还没有开始,主人公就消失。外公所有的希冀、念想以及香火传承,外婆都完成了,只是这一切耗尽了她全部心力,等到可以喘一口气时,她颓然躺下,从此追随外公,再没回头。
曾经担心,相隔多年的两人,还能相遇吗?还认得吗?想起外公唯一的照片,隐隐释然——应该认得,他从照片里望着这个女人,四十二载,终于团聚了。
外婆大名林琼珍,乡人多唤“安人”。
三
这些久远的故事,就像春天的草芽,一场雨后,注定冒出土层。
“外公(1910-1995)是近现代史上有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社员,一生酷爱诗词书画,即使是最困顿的时光,也没停止过追求。这张照片摄于1946年初,外公和妻儿战后重逢于湛江时拍的全家福。战时外公随广东省银行迁至曲江……外婆在日本投降后,再与外公团聚。”
这段文字及照片,题为“携手一甲子,荣辱从容度”,同样关于外公外婆,来自《广州日报》。当母亲说起此文时,已决定给作者写信。“广东省银行”这几个字,像一杆巨大的铁锹,撬开母亲心中那口七十多年的深潭。
七十年来藏在心底的泪水,怎能一次清零?母亲一天几个电话,还是说不完。我意识到,她沉浸在这种情绪里,会影响身体。然而怎么劝,还是一味回忆,就像一个任性小孩,吵着嚷着,要回到跟父亲母亲一起的日子。
记下来?试探着跟母亲说。电话那边,她有点迷茫,其實……其实我也就记得一点点,一点点,只记得我爸那几句话,死都记得。国难当头,为防万一,省行不得不要搬家,分南下北上撤退……她似乎陷入梦境中,断断续续。没关系,您想到什么说什么,小事情小细节都行,我记录下来,慢慢整理。那时候太小了。她怅怅地,嗫嚅着,不再吭声,梦境坠入黑暗,她茫然无措。唉,我从心里重重叹了一口气,却不敢出声,怕触动哀伤边缘的母亲。真难为,当年那么小,那么小就失去父亲,没有父爱的日子,怎么熬过来的?母亲从来不说。她只说自己六岁那年,独个从广州回台山,过了三个渡口,搭了三次船,每次都晕得呕黄水,天昏地暗,还是把包袱死死抱在胸前,一整天不敢松开,害怕人家抢;还说过,家穷迟迟不能上学,每天偷偷跟着小学生后面,听他们读书,把一本书的课文全背下来;又说,外婆跟着乡人卖故衣,把家中值钱衣服挑到阳江卖,然后换回粮食,一程走下来脚板都是血泡。回家后,母亲用小肩膀扛起外婆两脚,边揉边想,长大后一定不让呆妈(我妈)受苦……想起这些,心好酸,忙安慰她,都过去大半个世纪,不记得就算了,现在不是挺好吗?说着说着,却力不从心,仿佛抓不住的一些东西,正慢慢飘出视野。片刻,母亲好像突然从梦中醒来,对着话筒大声说,系靠系靠(是这样),我话你知……她在喘气。
平静下来,母亲说,大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具体哪一年不记得,有个自称陈叔的人辗转找到外婆,说有东西要交给她,是当年外公留下,嘱他代转。陈叔家在台山富城,但一直在外面谋生,年岁大了才回乡下。当年,他跟我外公一起在广东省银行工作,并同时撤到廉江。外公临终前,必定牵挂家中娇妻幼儿,必然想尽自己最后一把力,于是,身边所有值钱的物件:一袋银圆、金戒指、皮褂子——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交给这个信得过的同乡陈叔,嘱咐他想办法,转给台山锦昌村的林琼珍。
二十多年过去了。往事沉甸甸。
无法想象,异地他乡,濒临绝境,外公忍受怎样的生离死别,把最后的财物托付给他人;对家乡的亲人,又怀着怎样的愧疚和思念。隔着漫长的大半个世纪,外公的影像从模糊到清晰,焦点,就在这些遗留的财物上。外婆和大舅父一起去见陈叔,陈叔将保存了近三十年的东西取出,皮褂子已经当掉,银子也花去不少,只剩几枚,还有那只金戒指。母亲说,戒指见过一面,依稀记得圈上雕花,“好大只”。这样的东西,只能由大舅父留着保管。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我不太甘心。没有了……唉,就是那张照片。
就是那张,摆在外婆梳妆台上,长久盯着一家子的黑白照片。岁月悠悠,流转更迭,一个慈爱温暖的人,最后,就剩下这么一点念想。
四
信念,真是一种强大力量。进入暮年,母亲越来越坚信,那个拉着她的小手说“国难当头”的父亲,不会什么也没给她留下。也许世上哪个角落,会留有父亲的印记,半页旧笺,一角书信,几簇枯草,从中也许能读出,父亲对幼女的思念。
当我还在想,如何安慰一颗自小失怙的心,母亲,却早已开始自我拯救,以她的方式,寻找渺冥的痕迹。她给《广州日报》那个作者写信,“看到广东省银行这几个字,感觉很亲切,也很激动,几夜没睡好。这么多年,终于有了一点关于父亲的消息。也许,您外公是我父亲的同事,不知您家人有没有更多关于广东省银行的信息,能否帮忙了解一下?我……”她把手写的信笺交给我,却不知那个作者是谁?地址在哪?就像小孩,惴惴不安,似在恳求。
不敢怠慢,通过朋友找到《广州日报》版面编辑,对方通情理,马上告知作者电话。电话打去,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小朱,一位正在中山医学院读博的女子。小朱爱好文学,文史渊洽,对母亲的意思颇感惊讶,也很欣赏,她说不太清楚外公外婆当年的事,也许可以问问她的舅父……我的外公,她的外公,我们的外公年岁相当,又曾在广东省银行谋事,作为后人,我们像两只平行的小船,之前从没交集,而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刻,终于相遇。我感恩岁月的赠馈,但又担心,这样的因缘,能让母亲找到渴盼一辈子,哪怕一点半星的,父亲的信息吗?
另一丝留痕,则在广东湛江市。某天,母亲突然来电话,说出“湛江市廉江县塘蓬镇留村后山”这个地址。我正在上班,思绪在古板的文稿中游离,没反应过来。母亲加重语气强调:廉江,廉江。顷刻间回过神,廉江,当年广东省银行撤退的地方,外公最后日子停留的地方,母亲晚年念念不忘的地方。塘蓬镇留村后山,是外公茔墓所在地。母亲说。我拿笔快速记下地址,却发现,母亲只知道“留村”读音,不清楚哪个留字。她让我了解清楚,究竟有没有这个地方?现在能不能找到?她反复说这两句,我猜,还有意思没说出——如能找到,能否到现场拜祭,更深一层,能否把墓茔迁回来?
刚好,同事是湛江人。
打听。询问。百度廉江地图。甚至致电当地村委会,致电在廉江的台山人……又是一番追寻。
上下求索,还是缥缈无期。
年代久远,知情人少,关联物件几乎没有,这样的结果,亦在意料之中。所有的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何况信息星星点点,本就不辨真伪。
失望,混合无奈。混沌中,又有一丝欣慰,毕竟,了解一点点。只是,这么一点点信息,又如何抚慰母亲那颗苍老而期盼不断的心?
快过年了,花街、花市争妍斗丽,拍了照片给母亲看。新潮的妈妈会用微信,她熟练地拨动手机屏幕,一张张欣赏,边看边评,“这个靓,开得够精神”“月季,以前阳台也有”“这个什么花?奇怪,怎么没有叶子?”说着说着,不吭声了。探头看,是外公那张老照片。这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想起,便翻出看一会。外公浓眉大眼,额头敞亮,鼻子高挺,微侧身子站着。年轻,但沉稳老成,见折痕的西裤、口袋别着的钢笔、整齐后梳的头发,无不透着教养。但照片似乎翻拍,有点模糊,想从中找点什么,也是徒劳,只有岁月的沧桑,渗在微黄的背景中,烘托出那代人的坎坷。
“我爸总叫我阿雅”,母亲幽幽地说。心中一动,若说外公还有什么留下,就是母亲和大舅父的名字。大舅父“伟儒”,母亲“雅娟”,用字斯文,辞藻优美,儒雅相连,足见外公性情温润婉致,以他的聪颖上进,对孩子的祈盼厚望,当在自身之上,取名一事,深聚外公的心思。又想,当年撤离广州前,对母亲兄妹所说寥寥数语,“国难当头……”,亦知正当青年的外公内心,也有热血士子的胸襟。明知家人孱弱,这一去山高路远,不知何时相聚,但金融业乃抗日重要力量,银行撤离,事关经济作战重任,作为其中一员,他不可能临阵退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卑微如己,修身之外能做的,便是扛起全家六口的生计。外公最后给陈叔的托付,是倾尽他的所有,是对小家庭的深沉忧虑,也是一个普通人对家国的灾难深重,所分担的最大责任。思及這些,心里涌出无限伤感,既有对外公的刻骨怀想和敬意,更有对曾经家国沦陷的唏嘘。
2017年,农历丁酉年。母亲已逾古稀,找寻,作为内心一种牵挂和追念,也许贯穿整个生命中。她的执着不懈,让我渐渐走近外公,走近那个远去的时代,由此,更了解外婆,隔着几十年风雨,依然感受到那代人的风骨。年代刻痕,也延伸在母亲身上,她一直是家中主事,但凡族内红白喜事,生辰擢升,都打点妥帖,尤其对老一辈,人情心意,从不错失。我们,无论生活困顿与否,都是人群中从容写意的一家。她是父亲口中乖乖女“阿雅”,又是朋友间聪慧灵敏的“雅哥”,禀赋天性,一一都能找到出处。
当年,外公送给外婆的香云纱褂子,印着他们的手泽体温,历经大半个世纪打磨,从黑亮褪变为褐黄。家族的基因,在岁月的揉搓中,悉数收进一经一纬中,成为先辈留在我手上的唯一物件。女儿出生时,母亲用它做成婴儿枕头,一直用到褐黄褪尽,丝缕可见,如今,依然压着箱底。常常感叹,从外公外婆到母亲,自己,再到女儿,血缘就像一条河,细流激湍,波光潋滟,千回百转,从不改变方向,滋养我们的柔魂弱魄。
这条河的神奇,还在辗转流迁中,让母亲、弟弟和我的安身立命,最终选择了金融,冥冥中,能说没有外公的牵引吗?
溯洄从之,外公外婆就在水一方。
责任编辑:马小盐
猜你喜欢 外公外婆母亲 唠叨的外婆作文评点报·低幼版(2020年39期)2020-11-06我的外公小学生作文·小学低年级适用(2018年11期)2018-04-11外婆的钱小猕猴智力画刊(2017年12期)2017-12-27外公爱吹牛少年博览·小学低年级(2017年7期)2017-09-29外婆回来了作文大王·低年级(2016年12期)2016-12-21外婆的手初中生世界·九年级(2016年11期)2016-12-01外公的呼噜创新作文(1-2年级)(2015年12期)2015-12-17悲惨世界疯狂英语·阅读版(2013年2期)2013-03-22送给母亲的贴心好礼数位时尚·环球生活(2009年5期)2009-05-21母亲的养生谚饮食科学(2009年1期)2009-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