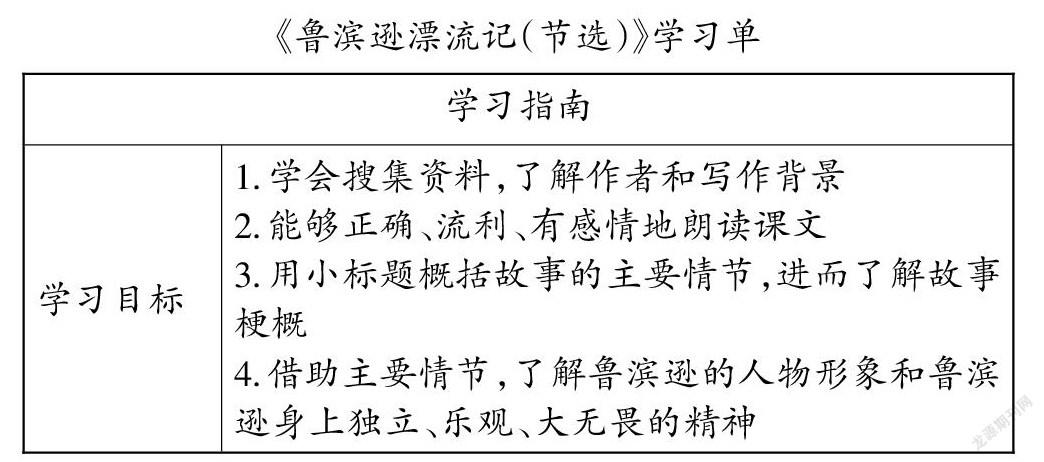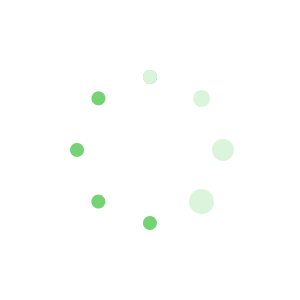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俄]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护人,一般说这些人也是作家。
只要读上几行这个鼓舞者的作品,自己便立刻想要写东西。从某几本书中好像能喷出酵母浆来,使我们心神陶醉,感染我们,使我们不自主地拿起笔来。
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家,守护人,在作品性质、风格和题材方面多半和我们迥乎不同。
我认识—个作家,是一个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他专门描写日常生活,人稳重而沉着。但他的守护人却是那位落宕不羁的空想家亚历山大·格林。
盖达尔把狄更斯称作他的鼓舞者。至于我呢,司汤达的罗马通信的任何一页都能引起我的创作欲,而且我写的东西与司汤达是那么悬殊,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有一年秋天,我读了司汤达的作品,便写了一个短篇《273护林区》,这篇小说是描写普拉河岸禁伐林的。但在这个短篇中全然找不到一点与司汤达的作品的共同之处。
不过说实在的,我并没寻找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可以找到的。我之所以提到这点,仅仅是想谈一谈,有许多粗粗一看并不重要的事情和习惯却能帮助作家们写作。
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在秋天写东西写得最出色。无怪“波尔金诺的秋天”成了惊人的创作力旺盛的同义语。
“秋天来了,”普希金写信给普列特尼约夫说,“这是我喜爱的季节——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壮起来——我的文学创作的时期开始了。”
当费定开始写他的长篇《不平凡的夏天》的时候,我刚好和他在一起。
我由衷地希望费定原谅我冒昧地写出这件事来。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作家特别像费定这样的巨匠的工作方式,不仅对作家们,而且对所有文学爱好者,都很有意思,而且不无益处。
我们住在加格拉紧临海滨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房子好像革命前廉价的“公寓”,是一幢体面的贫民窟。
每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它便为狂风和巨浪的冲击所摇撼,发出嘎吱嘎吱、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看就要塌似的。门上的锁都锈了,穿堂风一吹过,门便慢慢地、可怕地敞开来,停止几秒钟不动之后,又猛地“砰”一声关上,于是灰泥便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
所有新加格拉和舊加格拉的野狗都在这幢房子的露台下过夜。它们趁主人暂时外出的时候爬进屋来,躺到床上,心安理得地打起呼来。
不管盘据床铺的野狗的性子如何,进屋子时总要多加小心。狗不大好意思、羞答答地跳起来,失望地叫着跑出去。假如你碰着它的脚,它会因为恐惧而咬你一口。
假如碰上一条不要脸的老油子,它就会躺在床上,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你,可怕地叫起来,使你不得不请邻居们来帮忙。
费定的一面窗户朝着临海的露台。风暴咆哮的时候,把露台上的藤椅都堆到这扇窗子旁边来,怕淋湿了。狗总蹿在这堆椅子上,从上面望着在桌旁写作的费定。这群狗低声嗥着,想到他这有灯光的暖和的房间里来。
起初,费定抱怨说这群狗简直使他发抖。只要他的眼睛离开稿子,看着窗外开始思索时,便立刻看到几十只恶狠狠的眼睛盯着他。他甚至有几分不自在,好像因为他住在暖和的地方,却在白纸上画黑道,干着一种分明是无意义的事情而感到歉疚。
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费定的工作,但不久他便习惯了,不再理睬这群野狗了。
大多数作家在清晨写作,也有一些作家在白天,但绝少数在夜里。
费定能在任何时刻写作。仅仅是偶尔歇歇乏才停下一会儿。
他每夜在大海的呼啸声中写作。这种听惯了的喧嚣声非但不妨碍他,甚至有助于他的文思。相反,寂静倒使他烦乱。
有一次,在深夜里,费定把我叫醒了,焦灼地跟我说:
“你可知道海沉默了。我们到露台上去听听。”
一片深沉的、好像非常静穆的沉寂笼罩着海岸。我们默不作声,想要在黑暗中听到哪怕一声微弱的浪花拍溅声,但是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耳膜嗡嗡地响着,这是我们的血液流动的声音。在高空,在那弥漫苍穹的黑暗中,撒着几点朦胧的星光。我们习惯了这大海的喧声,甚至为这种静寂所窒息了。费定在那一夜里没有写作。
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不得不在他所不习惯的环境中工作。我以为这种生活的朴素与简陋使他想起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我们能够在窗台上,在洋油灯旁,在墨水都上了冻的房间里,一句话,在任何条件下写作。
我无意中观察了费定,才发现他只有在把下一章严格地考虑过、调理过、用沉思和回忆充实过之后,直到个别字句都在思想中推敲成熟的时候,方才下笔。
费定在动笔之前,全神贯注地从各个角度来审查这部未来的作品,他只写他深思熟虑过的、轮廓分明的、同时和整体有完整的关系的东西。
费定的明豁而坚定的智慧和严峻的目光,不容忍那构思和表现的模棱两可。按照他的意见,散文应该写得确切无瑕,锤炼到金刚石的硬度。
福楼拜在文字的惨淡经营中度过了一生。他不能够停止追求散文的晶化。有的时候,对他说来,修改稿子并不是使散文完美无瑕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了。他失去了鉴别的能力,疲惫不堪,悲观失望,而且显然地枯竭了,把自己的作品弄得没有生气,或者如果戈理所说的,“描写呀,描写呀,变成个描写迷了”。
费定知道在琢磨文句时应该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他身上的批评精神从不疲倦,但也没有让作家灰心。
在福楼拜身上高度地表现了那种文学理论家们称做作家的“人格化”的特性,简言之,这是一种禀赋,作家以强烈的力量,使自身与人物合成一体,亲身极其痛苦地体验作品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的一切。
如所周知,福楼拜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临终之际,他自己也感觉到中毒的种种症候,因而不得不向医生求救。
福楼拜是一个痛苦的人。他写得那样慢,他自己绝望地说:“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真应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他住在卢昂附近塞纳河畔的克鲁阿斯。他书房的窗户便临着塞纳河。
在福楼拜的有异国情调的书房里,终夜点着有绿罩的灯。福楼拜在夜里写作。到晨光熹微的时候灯才熄灭。
灯光是通宵达旦的,好像灯塔。真的,在暗夜里,福楼拜的窗户成了塞纳河上渔夫们的灯塔,甚至从哈佛尔往卢昂溯游而上的海轮的船长们也把它当作灯塔。船长们知道在一段航路上要想不迷失方位,应该“以福楼拜先生的窗户”为目标。
他们偶尔看见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身穿一袭华丽的东方式的睡衣。这人常常走到窗边,前额贴在窗上,望着塞纳河。这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的样子。但那些弄潮儿却未必知道窗子里站着的是一位法国的伟大的作家。他为争取散文——这个“可诅咒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定型的、没有形状的东西”——的完美,已经精疲力竭了。
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工作。他说每一个作家身上都具有一种批评的精神。这种最尖苛的批评精神经常在早间出现,夜里便酣睡不醒,所以在晚上,作家完全是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地工作,于是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托尔斯泰举出卢梭和狄更斯的例子,他们都只是在早晨写作,并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伦就因为喜欢在夜里写作,而违背了他们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累赘当然不只是在于他在夜里写作而且不断喝茶。这毕竟不怎么严重影响他作品的质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繁累在于他总没摆脱贫困和债务,所以他被迫多产而且总是仓卒急就。
他总是迫不得已时坐下来写作。他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平平静静全力以赴写出来的。他总是草率地结束自己的小说(不是按照写好的篇幅的数量,而是按照叙述的广度)。所以他的作品比它们可能有的样子和原来构思的样子坏得多。“想的远比写的好,”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他常想和他未写完的小说在一起多留连一些时候,时时修改和充实它。所以他拼命拖长写作时间——因为每天每小时都会产生新的思想,当然不能把这些新思想倒填进去。
债务逼着他这样做,虽然当他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常常意识到作品还没成熟。多少思想、形象、细节都白白地放过去了,就因为它们浮现在脑际时,已经为时太晚,不是小说已经写完了,便是在他看来,已经无可挽救了!
“由于贫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自己,“我被迫为金钱而匆忙写作,所以接二连三地失败。”
席勒只有喝完半瓶香槟,把脚放到冷水盆里才能写作。
契诃夫年轻的时候能够在莫斯科拥挤而嘈杂的住宅的窗台上写作。而短篇《猎人》是在浴棚里写的。但这种满不在乎的习惯已逐年消失了。
莱蒙托夫把自己的诗写在随手抓到的东西上。这些诗篇总好像在他的意识中顿时形成的,它们先在他的灵魂里歌唱,然后他才急急忙忙把它们一字不改地记下来。
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假如在他面前摆上一叠洁净的上等质量的纸,便能写作。他曾坦白地说过,他坐下来常常不知道要写什么。在脑子里先有一个生动的细节。他从这个细节开始,而这个细节像一条魔术的线似地逐渐引出全部故事来。
托尔斯泰照他自己的说法,把工作状态、灵感叫作来潮,“假如来潮,”他说,“我写得便快。若是不来潮,那就得搁笔。”
当然,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即兴作家。他的思想总使他下笔神速。
写作之际即当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突然涌现,从意识的深处像闪光一般冲到表面上来的时候,这种绝妙的心境是每个作家都亲身经历过的。假如不立刻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同样会消失得无踪无影的。
其中有光,有颤动,但它们像梦一样易逝。有一些梦,在我们刚刚醒来的那一瞬间,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断,但立刻便忘了。以后无论我们怎样费尽苦心,无论怎样努力想回忆,总归徒劳。这些梦只残留下一种异样的,谜一般的东西的感觉,若是果戈理,他就会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东西”的感觉。
应该马上记下来。一秒钟的滞延,这思想会倏然一现便永远消逝了。
安徒生喜欢在森林中构想他的童话。他有极好的、差不多是显微镜般的洞察力。所以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观察一块树皮或一颗老松球,并且像通过放大镜一样精密地看到这些东西上的一切,用这些微小的细节很容易地编成童话。
总之,林中的一切——每一根覆满苔藓的残株,每一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们曳着绿色透明小翅的虫儿,好像拉着窃来的美丽的公主一般——都可以变成童话。
我本来不愿谈自己的文学写作经验。这未必能给上文谈到的增添些什么重要东西。不过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说上几句话。
假如想使我们的文学无限繁荣发展,那么必须明白,一个作家的社会活动的最有成效的形式,便是他的创作工作。在出版前为大家所不知道的作品,一经出版,便成了全人类的事业。
应该珍惜作家们的时间、精力和才华,不要在累人的文学以外的忙乱上浪费它们。
作家在工作时需要安静,尽可能没有操心的事。假如有什么事等着要做,甚至是细微的烦恼,那最好不要提笔。不然不是笔从手里滑下来,便是写出勉强挤出来的连篇废话。
我一生中有几次在写作的时候心情輕松,注意集中而且从容不迫。
有一年冬天,我坐一艘内燃机船从巴统到敖德萨去。船完全是空的,什么也没装。海面一片灰色,寒冷而平静。海岸隐没在灰色的烟雾中。浓重的乌云,好像在迷梦中,横在迢迢的山岭上。
我在客舱里写作,有时站起来走到舷窗旁看海岸。强大的机器在内燃机船的钢铁的内舱里轻声地歌唱。海鸥呷呷地鸣叫着。写起来感到轻松。谁也没打断我珍贵的思路。除了我正在写着的小说而外,什么也不用想,一丝杂念也没有。我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辽阔的海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的烦扰。
在广阔的海洋上行驶的威觉,对我们要登岸的许多港埠,或者对一些令人亢奋的偶然邂逅的模糊期待,都大大地帮助了写作。
钢船首划开了惨白色的冬日海水,我觉得这艘船正在把我带向那命中注定的幸福中去。我这样想,显然是因为小说写得很成功。
我还记得,一年秋天,我一个人在一座木房的顶楼上,在灯花爆炸声中,工作得多么顺利。
暗黑的、无风的九月之夜,也像海一样包围着我,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烦扰。
窗外乡间花园彻夜在飘零着落叶的感觉,很难说出理由来,但是大大地帮助了写作。我像思念一个人似的怀念着这座花园。它安详沉默,耐心地等着我在夜晚到井边去打水烧茶。当它听到水桶的哇哇声和人的跫音时,或者可以减少一点忍受这漫漫长夜的痛苦吧。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荒凉孤独的花园,村子四周蜿蜒数十里的寒林,林中的湖水——当然,在这样的夜里,湖畔绝无人影,只有星星和千百年前一样倒映在水中——这一切给人的感受都帮助了我的写作。我敢说,恐怕在这样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
当一种有趣的、欢乐的、心爱的事情,甚至像到远处的旧河床边垂柳下去钓鱼这类小事情在前面等着你,你都会写得很出色。
(千年书虫选自《金蔷薇》,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猜你喜欢 陀思福楼拜作家 大作家笔下“失落的世界”少年博览·小学低年级(2020年11期)2020-12-14作家阿丙和他的灵感故事作文·低年级(2020年8期)2020-08-17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者(2019年1期)2019-01-13福楼拜的『笨学生』东方少年·阅读与作文(2018年1期)2018-05-14我和我的“作家梦”阅读(低年级)(2018年7期)2018-05-14来吧,与大作家跨时空PK吧!课堂内外·创新作文小学版(2018年12期)2018-03-01莫泊桑拜师文理导航·趣味课堂(2017年3期)2017-08-22传世名著的背后中外文摘(2014年23期)2015-04-15特长就是专心地做一件事情家教世界·创新阅读(2009年3期)2009-04-17安尼娅的白手帕慈善(2009年2期)2009-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