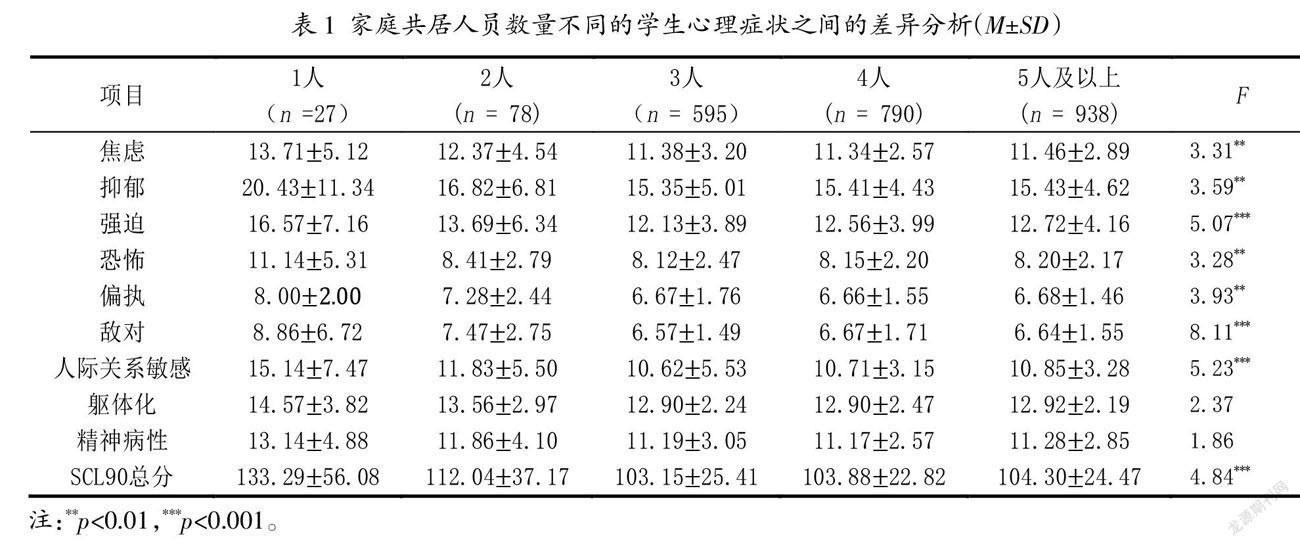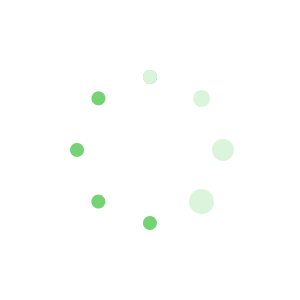芽姜
雍青想着,脸上泛起微笑了。过往亲人之间的那些龃龉和不合适恋人的那些情事在心底蠢蠢欲动,它们似乎都化成黑色的飞蛾,纷纷扇动着翅膀,从雍青身体黑黝黝的空洞里飞出去,扑棱棱地飞向冰雪的世界里,消失不见了。
四四方方的麻将桌上,麻将哗啦哗啦地搅匀在一起,几双手凑在一起麻利地码成四摞,饱满的白色朝下,悦目的绿色在上,安静地等待着牌桌上的人揭开下一张牌的谜底。
“这打麻将啊,就像是人生!”三姨吐掉嘴里的瓜子壳,伸手去抓一张新牌,“不摸到手里,这再好的牌也不是自己的。”
雍青听了话,只是扯扯嘴角笑了笑,余光却瞄向了母亲。母亲面上没什么,左手却一直转动着手里的麻将,厚重的麻将重重敲击在桌面上,一下一下,像是在提醒雍青什么。
“哎——胡了!”新牌亮相,三姨挂着黑色瓜子屑的嘴唇咧开,堆满笑容的脸朝向母亲:“你看,这好牌不就到手了!”
母亲细细的眉毛微微扬了扬,修长的手指掠过码得整整齐齐的麻将,那种自然又不在意的神情挂在脸上,“三姐又胡了,今天真是好运气。”
像是从前雍青绘画比赛没有得第一名时的样子,母亲对着那些熟人家长说:“没什么的,我们家雍青常拿第一,下一次努力就好了。”
牌又打了几圈,雍青陪下来,全身又酸又软,比画一天画还累。她趁着别人出牌,支着头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往下掉。
小姨开了口,“青妮儿,去你玲姐房间休息会儿吧!”
雍青眼睛瞇着,半梦半醒,还没回话,三姨笑道:“那可是新房,青青去可不好!”
小姨吐吐舌头,“这玲玲一结婚就去旅游,十天半月不在家,我都忘了她都结婚了这一档子事!”
母亲轻轻敲敲牌底,像是感叹:“这小姑娘,转眼就长大嫁人了。”
三姨眼睛从牌上拿开,对母亲笑道:“这青妮儿的好事什么时候到?”
母亲手上顿了顿,牌不响了,雍青更加如坐针毡了,小姨见势头不对,挑了张牌落下桌,岔开了话:“一饼,碰不碰?”
“碰了!”三姨把牌收到手中,笑逐颜开地说道:“这把又胡了!”
雍青住的地方离小姨家不远,隔着两条小巷一条马路,所以无论小姨怎么留,雍青也要回出租房去住。
走的时候母亲坐在沙发上吃红提。天花板上层层叠叠坠下水滴状的吊灯,蜜糖一样的灯光把母亲包裹,她葱白细长的手指捏着浅紫色的红提,一丝丝地剥下皮,温柔又小心。像是从前教雍青学走路时候的温柔小心。可直到雍青关上门,母亲也没有转过来看自己一眼。
回去途经的小巷没有灯,昏昏暗暗的,雍青开着手机的光照明,偶尔路过一只猫或者一个醉汉,她就小心地贴着墙边走。路不长,沿路爬山虎的叶子已经变得苍翠,夜风吹来窸窸窣窣作响,雍青听到也会往外走远一点。
爬山虎里有蛇。
惠修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夏天,雍青正在厨房里炒惠修最爱吃的辣椒炒肉。
厨房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油烟机哄哄哄地响,可是油烟味一点也没有排出去。雍青站在烟熏火燎里,也听不清楚,一边呛着一边走出来问,“你说什么?”
“爬山虎里有蛇。”惠修把手机游戏暂停了,重复了一遍。
“哦。”雍青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没去想惠修无端说出来的话,走过来亲近他,“什么时候我们才换一个油烟机?”
“不是早让你通知房东?房东会修的。”
雍青没说话,眉头皱了起来,看着惠修。
惠修眼睛还在手机游戏上,没得到回应才抬起头看雍青,“好好好,我明天就找人换。”
雍青捏着拳头,作势要揍他,拳头还没落下来,惠修假装倒了下去,“青青你不爱我了!”
“小狗才爱你!”
雍青气鼓鼓的话还没说完,惠修一伸手就把她揽在怀里亲亲她,雍青的气一下子就都没有了。
寂静的小巷里,夜风凉凉地吹起,地上的影子晃晃悠悠,爬山虎的叶子依旧簌簌作响,雍青莫名想起的这件事,好像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了。
“你下班了吗?”雍青垂着头,把短信发给那头的惠修。
不一会儿就收到惠修的回复:“今天可能要工作到凌晨,你不用等我了,先睡觉吧。”
“嗯。”
虚无缥缈的短信随着电波漂浮在看不见的地方,雍青一步一步爬上七楼的老式公寓,打开门忽然觉得房间里面都是灰尘。
雍青搬进来这里已经五年了。从大学刚毕业的新鲜,到现在快要二十八岁的雍青,已经五年过去了。
母亲很少给雍青电话,第二天一大早稀罕地打来问她,“他打算什么时候娶你?”
母亲年轻时是出色的钢琴家,受过无数赞誉也见过无数场面,她总是给人一种波澜不惊的感觉,包括对雍青的催婚,雍青也能想象母亲在电话那头蜻蜓点水,毫不在意的样子。
可这话却是步步紧逼。
他什么时候娶你?
说明母亲已经知道,娶她这件事,雍青已经做了十万分的准备,只是在等男生的开口。
母亲的语调像是钢琴曲谱中最低的C调,没有任何起伏:“你该不会廉价到,连求婚也要你去求周惠修。”
母亲的话在雍青脑袋里转了几圈,像是小时候玩的跳跳球,落下弹起,撞得雍青晕晕乎乎的,撞得雍青满肚子的气也漏了出来,“不用你管!”
挂了电话,雍青才开始后悔,再打过去电话就变成忙音。
好像全部都是雍青的错似的。嫁不出去的姑娘,看笑话的三姨,丢不掉的架子和面子,母亲的烦恼雍青样样都清楚,可雍青的麻烦,谁也不知道。
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哐哐响了几声,钥匙叮叮当当地响,雍青摊在发灰的沙发上,眯着眼,连看一眼进来的惠修都没有力气。
惠修把电脑包扔在沙发上,脱下外套往厨房里走,“有什么吃的吗?”
“冰箱里有速冻饺子。”
“只有速冻饺子?”惠修似乎不满意,转了一圈出来朝半躺着的雍青撒娇:“饿死我了,青青你帮我煮个饺子吧。”
雍青有气无力的回他:“我有点累。”
“青青,”惠修过来想拉她的手,雍青躲了过去,惠修才发现她有些不对,“怎么了?”
“昨天去了小姨家。”
“你们家亲戚——”惠修欲言又止,避开这个话题,“你吃饭没有?我给你也煮一点。”
“不用了,吃不下。”雍青转过脸去,不想看他。
惠修蹲下来同她说话,“你妈又说你了?”
雍青摇摇头,又转过脸去不说话。惠修也不说话了。小房间里忽然静得可怕,只剩下冰箱上挂着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小小的房间似乎比雍青一个人的时候还安静。
“姜雍青,”惠修静默了很久才开口,一字一句的念着她的全名,“你又怎么了?”
雍青没说话,别过去的脸皱在一起,鼻子酸酸的,眼睛也雾蒙蒙的。她究竟怎么了?雍青想跳起来质问他,我怎么了你不清楚吗?
那话酝酿在心头许久,直到惠修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也没有说出口。
雍青和惠修是在大学里谈的恋爱,可惠修说,早在之前的好多年前,他就喜欢上了雍青。
那样优秀的雍青,很小的时候就饱受天才画家的赞誉。惠修说,他从前听说雍青的时候,以为会是一个不羁的人,可他在少年宫见到的雍青安安静静地坐在画室里,一个人在黄昏的时候,执着画笔涂抹油彩。
惠修说,那时候的雍青还小小的,眼睛狭长,皮肤白皙,橘色的余晖照在她翘起的鼻尖上,就像是天使。所以后来他在大学里见到雍青后,立即就决定追她。
“幸好那么美好的你没有被别的男生抢走。”惠修表白的时候这样说,未经感情的雍青听不得情话,脸红红的,像是喝醉了一样,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了他。
他们的恋爱受尽祝福,惠修也愿意包容雍青的一切缺点。后来毕业了,雍青为了画画,在外租了房,惠修也搬了进来。他开始找工作不顺,雍青放下画笔来安慰他,后来他找到了工作,每日忙忙碌碌,雍青就放下画笔来照顾他。
过往的一桩桩,一件件,在雍青脑子里通通过了一遍,这短短的小半生像是下水道的流水,哗啦一声便一去不回来了。
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感情慢慢降温了?
这个问题像是一道惊雷,炸開了雍青心中一直紧绷的弦。雍青原本半眯着的双眼忽地睁开,斜阳坠了下来,阳光落在纱窗上投下细密的影子,像是一只逃不开的网。她想不出来答案,只觉得全身发烫发软,摇摇晃晃地起身去拿温度计含在嘴里。
三十八度半,雍青甩了甩温度计把它归位,披着外套一歪一歪地出门去楼下的诊所看医生。
医生开了三天的点滴,雍青输完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躺在床上的时候,母亲给雍青发消息,问她有没有同惠修商量结婚的事。雍青正无聊地刷微博,看到母亲主动发消息,赶紧回复过去:“今天有点发烧,没想这么多。”
“周惠修呢?他没照顾你?”
雍青一边小心翼翼地沿着母亲给的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一边维护自己的脸面,“他还在加班。”
“加班。”母亲轻轻重复了这两个字,语气里充满的不屑与嘲笑似乎想让说谎的雍青脸红。
一股气蹿了上来,雍青瞪着屏幕上母亲的回复,拿手机的手指捏到发白。她想起为了得到母亲赞许,疯狂练习画画的自己、想起因为惠修迟迟的不肯求婚让母亲丢脸的自己、想起小心翼翼顺着母亲高贵台阶往下的自己,她是母亲的面子与里子,她的不堪就是母亲的不堪,她的底色就是母亲的脸面。
可雍青累了,她顾不了这么多。直到手机幽幽的光熄灭,深海一样深邃的黑暗翻涌着浪头,一次一次地将雍青吞没,这一次雍青没有再回复母亲什么。
第二天雍青去打点滴的时候,在楼道里遇见了惠修。一夜未归,他的下巴冒出一层浅浅的青色,连头发似乎也长了些许。他看着雍青憔悴的样子,似乎有些关切,“你怎么了?”
雍青的语气干巴巴的:“有点发烧,去楼下打点滴。”
惠修点点头,没有话可说,他垂下头侧身留出很宽的路让雍青。雍青向他走过去,同他并肩的时候试探地问他,“你同我去吗?”
惠修愣了一下,随即点头。
打点滴的时候漫长无聊,互有怨气的情侣尴尬地对视后又错开眼神,惠修和雍青,谁也没有先开口。也不知道多久,惠修趴在病床边睡了过去,雍青放下装模作样的手机,低下头来看他。
他的眼睛很小,鼻子很大,嘴巴抿成一条细细的线,看起来像是在为什么为难。他的鼻息很轻,圆钝的下巴上长出一层青青的胡茬,雍青伸出食指轻轻点上面,却把惠修惊醒了,两人颇有些尴尬的对望。惠修先开口:“药输完了,我去叫人。”
惠修起身去找护士,回来的时候神色如常,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回家后两人也静悄悄的,雍青回了卧室,留惠修一个人在客厅。等到一阵糊味传进来的时候,没有修的油烟机才开始轰轰轰地运作,雍青跑出去看,惠修在厨房丧气地端着一锅黑乎乎的粥。
“我想熬粥给你喝,”惠修的表情有些可怜,像是孩子一样讨饶。“你看,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好。”
他的让步一向有用,雍青鼻子有点酸,惠修放下锅把她拢在怀里,“不生气了好不好?”
“嗯。”雍青将头埋在他的肩膀上,委屈一股脑地跑出来,眼泪也止不住了,统统蹭在了惠修的衬衣上。
“我还有惊喜哦!”惠修拍怕雍青的脊背,变魔法似的掏出来一个小小的黑色的长方形丝绒礼盒,“打开看看。”
雍青疑惑地接过打开。是一枚戒指。
光滑的银环上,一颗小小的碎钻倒映着细碎的灯光,它半边藏在黑色的衬垫里,像是雍青可望不可即的梦。
“这几天我想了许久,我应该给你一个家,给我们的感情一个交代,”惠修单膝跪在地上,一只手高高的举起戒指,“青青,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请嫁给我吧!”
雍青像做梦一样,由着他把戒指套上自己的无名指。闪着银色光泽的戒指空空荡荡的挂在上面,雍青觉得有些不合适,可她觉得没关系,脸上依旧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婚礼定在十月,母亲同惠修的父母简单地见了一面,剩下的事情都由惠修和雍青自己决定。
婚纱照、请柬、婚庆、场地,一样一样地挑过去,雍青从来没有这样忙过。等到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了,雍青就专心选婚纱和礼服。店子是表姐玲玲介绍的,据说老板是个眼光毒辣,风格鲜明的姑娘,雍青一听就喜欢上了。
雍青按着表姐给的地址找过去,婚纱店开在偏僻的巷子里,门口有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爬山虎,风一吹过来,无数的小叶子就沙沙地摇摆起来。雍青从没有这样愉悦过,她隔着玻璃橱窗看里面精心装扮的模特,洁白的婚纱赋予它们灵魂,雍青想象中,她穿上时也会这么美。
雍青同惠修约定好了一起来看婚纱,惠修说晚一点在婚纱店集合。她忍不住,先推开玻璃门走进去,电铃机械地喊出的欢迎光临吵醒了午后空空荡荡的小店,不多时年轻的女老板就出来招待。从婚纱挑到礼服的时候,女老板随口问道:“您先生怎么没来?”
雍青似乎是突然想起来惠修,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她甚至连一条惠修解释的短信也没有收到。雍青忽然想起这样信誓旦旦要娶她的惠修,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婚礼的筹备。可雍青像是会撒谎的惯犯,她坦然自若,越来越有母亲毫不在意的风范,“我先来看看,下一次我们再一起来。”
女老板自然不会深究,她带着雍青一件一件的挑选,试穿,记下雍青的尺寸和爱好的风格,在雍青付下定金的那一刻全心全意地祝福道:“愿您与您先生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雍青拎着女老板送的小礼品礼貌道谢,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隔着透明的玻璃橱窗,她看见急急奔来的惠修。
爬山虎里有蛇。
雍青不知怎么想起从前惠修无端说的一句话。
是什么时候他们的感情开始降温的?
当雍青开始在母亲的催促下愁嫁,当惠修一次又一次因此而闪躲,当惠修总是在加班,当雍青不懂惠修说的话。当这一切发生之后,平静的爱情被日复一日消磨,如同枯燥的,重复的,外面一直簌簌响着的爬山虎,那里面随时都可能会窜出一条咬人的蛇,给这段关系致命的一击。
惠修求婚时说,感谢她这么多年的照顧。这个让她付出多年青春与爱的男人,原来是在同自己做等价交换——流逝的青春与结婚,他大概是觉得自己可怜,是成全了自己。
黄昏的阳光在光洁的地板上铺开,迟到的惠修打开玻璃门,清脆的机械女声喊出一句欢迎光临,雍青冷静自持,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心里有什么东西也跟着熄灭了。
母亲让雍青晚上去小姨家,一起参谋婚礼伴手礼样品。天灰灰地下起雨,雍青走得磨蹭,母亲打来电话催了几次,到达小姨家楼下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小姨留了门,雍青无声无息推门进去,谁也没打扰。在玄关脱了鞋进去,两个表弟正围在一起打游戏,两个姨夫正喝着茶下象棋,母亲和三姨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小姨端菜出来,看见雍青,似乎是喜迎什么贵客,笑道:“青青来了!”
她声音刚落地,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脸上难得有了笑容,“婚纱选得怎么样?”
雍青避开她的眼神,“嗯,还可以。”
“就等你开饭了!”
三姨把最后一道菜摆上桌,两个表弟围上桌,姨夫们坐了过来,母亲脱下围裙也坐到了雍青身边。
三姨似乎也是喜气洋洋,“青青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领证?”
“最近日子不好,我看下月初就可以。”小姨抢先答话,又问雍青:“伴手礼的样品带了吗?拿出来大家看看。”
“着什么急,”母亲有些嗔怪,更多是喜悦,“吃完饭咱们慢慢看。”
雍青埋头送了一口白米饭进嘴,含含糊糊地回道:“样品忘带了。”
“忘带了?”三姨脸色有些不好,“你妈不是说嘱咐了你几次——”
小姨伸手扯了扯三姨的衣摆,止住了三姨的话头,“没事儿,下次再带来咱们看!”
雍青点点头,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桌上的气氛变了变,像是无端积了朵阴云在头上,谁也没有说话,只剩下叮叮当当吃饭夹菜的声音。
离开小姨家的时候,母亲主动说要送一送雍青,雍青换鞋的手颤了颤,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看出来什么,抬起头说不用。母亲站在窄窄玄关的那一头,背着灯光,双手插在裤袋里,瘦小的她似乎又变得和幼年雍青眼中的母亲一样高大。她看着雍青,那样的姿势与沉默,不容推脱,雍青也就由她送。
似乎又下了雨,楼下的积水未干,坑坑洼洼的地面淌着一地的灯光,被雍青一踩,又迅速碎了。
母亲先开口:“你怎么了?”
雍青没有说话,母亲停下步子,没有起伏的语调再次重复了一遍,“雍青,发生什么了?”
“我不结婚了。”雍青转身看她,似乎有点破罐破摔的意思。
“为什么?”母亲不可思议地看着雍青,“你如果任性,也别拿这种事开玩笑。”
雍青靠近母亲几步,低下头,像是小时候做错事一样认罚。也许母亲因为太过丢人不要她了,或者母亲再也瞧不起她,或者,她想过许多,但是说出来也只是寥寥几个字,“我没有开玩笑。”
雍青花了一个上午从出租屋里搬了出来,收拾东西的时候才发现没什么好带走的。惠修坐在客厅里,静静的看着雍青,直到雍青把箱子拎到了门口,惠修也没有开口说一句挽留的话。
这场感情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束得无声无息。雍青独自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想起从前没钱的时候一起吃过的一碗泡面,想起生病的时候惠修的怀抱,想起惠修说过的那些誓言和情话,这长长短短的小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很久以前的事情。静默的午后,连司机话也不多,她把车窗打开,风呼呼地灌进来,她别过头去,把眼泪也吹干了。
雍青没来得及找房子,只好搬回去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认为雍青任性,不给自己留情面,没说出口的责怪隐隐发酵着,对雍青的态度愈发冷淡。从不知道如何开口解释缘由到觉得没必要解释,雍青只是沉默,生活重心放在绘画创作上,整日闷在家里,掩耳盗铃似的逃避着。
婚礼的事情暂时搁置,雍青还没有勇气通知取消,可是请柬已经送了出去,婚期也越来越近,母亲焦灼地在房子里提醒雍青:“你通知的婚期还有一个月。”
雍青支著画板,背对着母亲,没有回答她。
“你知不知道她们会怎么说你?”母亲走上前来,像是要做一个传声筒,“一个取消婚礼的女人,是弃妇啊。”
母亲的语气淡淡的,像是在转述一件与雍青无关的事情,仿佛这些扎人的话,并不是流言中伤害雍青的那些。
雍青想起从前画画比赛得了第二名的时候,母亲也是这样告诉年幼的自己:“你知道他们怎么看你吗?拿第二名的人永远都是失败者。”
雍青知道母亲心中有一杆秤,秤的一头是别人的评价,秤的另外一头是雍青。如今雍青这一头越来越轻,别人的评价越来越重,雍青知道,到哪一天,别人的评价将自己撬离母亲的心,始终泰然的母亲,或许只会轻轻皱皱眉头就没有了。
雍青垂着眼,那样的念头一闪而过,手里的画笔继续舔饱了颜料,猩红的颜色涂抹在纸上,像是胸腔里流出的鲜血。不知为何,离开了惠修后,雍青反而释放了许多,原本阻滞的灵感忽然通畅,多年来未有的佳作一挥而就,连雍青都想象不到自己能够画出这样的作品。
雍青像是着了魔,誓要将心头血都洒在画布上,母亲轻飘飘的话像是来自另外一个维度。直到一只修长细白的手突兀地挡住视线,鲜红的画布哗啦一声被扯出画架,瞬间被撕成碎片,雍青才回神过来,看见母亲原本平整没有波澜的脸上有了一丝愤怒,一丝不甘。
母亲的白色衣裙被红色颜料污染,她指着雍青的鼻子,恨铁不成钢地责骂:“你究竟想做什么?你若是想报复我,也别拿自己的一生做赌注!”
雍青从没见过这样的母亲。她望着母亲,扯破的鲜红画布像她的心一样,仿佛汩汩地要流出血来。她沉默了很久才回答:“他不爱我了。我不想为了你的面子,将就一辈子。”
她的声音不大,像是幼时做错了认罚,却又不像,更多是在发泄。她看见母亲愤怒的脸上露出无法言喻的表情,有些滑稽,有些好笑,是雍青这辈子没见过的样子。真痛快啊!雍青想着,对母亲扯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取消婚礼的事情很快传开了,母亲一家一家打电话去解释,原本挺拔清瘦的脊背,一瞬间也弯了不少。雍青比从前的话更少了些,她避着母亲,又常常偷看母亲的脸色。
母亲同雍青似乎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她打了几天的电话,夜里勾着背,戴着老花镜,一个一个按着电话本的号码拨过去。灯下灰白色的飞蛾朝着炽热的灯泡撞去,呼呼地扇着翅膀,扰得母亲不安,她挥挥手,把蛾子赶开,转头的时候看见雍青在门外站着,原本夸张的动作一下子收敛,她的表情有些僵硬,最后还是招招手唤雍青:“进来坐吧。”
雍青有些拘束地坐在母亲的旁边。母亲没说什么,细长的手指继续拨着号码,老式的座机按键滴滴作响,呜呜地拨通了,那头的人似乎已经知道了,安慰母亲几句便挂了。
如此往复,雍青只静静的坐着。蛾子在头顶上叨扰,奶油似的灯光下,母亲原本洁白光滑的皮肤似乎有了褶皱,老花镜下的双眼浑浊无光,从前高高在上,一心好强的母亲好像,变小了变弱了。
母亲挂断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珍重得像是放下自己的尊严,她低着头看了座机上亮着的屏幕许久,抬头看见雍青愣愣地瞧着自己,仿佛幼年时雍青玩弄坏掉的钟表,许久才会走到下一秒钟,顿了许久,母亲朝雍青笑了。
是开怀的,毫无芥蒂的笑了。雍青从来没有见过母亲这样的笑。她一面笑着,身体却开始慢慢变小,头发也慢慢变得花白,连一直昂起的头也慢慢低了下来,似乎周身都变得温和起来。
母亲老了。一个声音传入雍青的脑海,连雍青自己也没有反应过来。
雍青在三十二岁这一年,终于要嫁人了。
对方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笑起来很憨厚,同雍青小时候梦想的白马王子一点也不一样,却是会永远向着雍青的人。
母亲知道的时候很开心,她坐在轮椅上,好不容易清醒一些,开怀地笑起来,露出满口白花花的假牙。控制不住的口水顺着嘴角一路滴到胸前,她满不在乎,像是个得了梦寐以求玩具的孩子。
母亲是在雍青同惠修分手的那一年检查出来老年痴呆的。小姨说,母亲的病是早有征兆,她有时候找不到回家的路,又瞒着雍青,小姨只好给她装好自己的联系电话,后来干脆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住。只是雍青没有发现,与母亲见面总是在小姨家里。
雍青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看出来,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隐瞒自己。
糊涂的母亲时常穿着不一样的袜子,出了门就忘了回来,后来病情越来越重,手脚开始不听使唤,有时候连雍青是谁也搞不清楚。这么些年来,雍青辛苦照顾,却觉得这是这辈子最接近母亲的时候。
温柔的母亲,紧紧依靠着自己的母亲,不再高高在上,是能触摸到的温暖。
好在贴心的新郎包容雍青的一切,连同她生病的母亲。他心疼雍青,婚礼一路下来,没有让她操一点心,只在试婚纱的时候,新郎一定要雍青选一套最喜欢的,一家一家的试下去,不厌其烦。
结婚那天是那一年的初雪,细碎的雪花洋洋洒洒地落下,高高低低的建筑被覆上薄薄的积雪,整座城市都是浅浅的灰白色。办婚礼的小酒店却热闹非凡,雍青与新郎举杯共饮,鲜花掌声祝福包围着他们,在所有人的见证下,雍青同新郎交换戒指,那是刚刚好圈住雍青幸福的戒指。
雍青从众人的目光中谢幕,走到台下的时候几乎快要落泪。母亲也跟着众人欢呼鼓掌,她笑中带泪,却看不出来究竟是不是清醒的。雍青走过去拥抱她,她手脚不受控制,许久才将手挪到雍青背上,轻轻拍打。
“青青,青青……”
母亲喃喃自语,雍青看着她没有焦点的双眼,觉得母亲似乎回来了。
“我怕没有人,”母亲继续断断续续地说着,“没有人照顾你。”
母亲病情的隐瞒与冷冰冰的催婚被联系在一起,雍青似乎是一瞬间反应过来了,过了许久才惊觉有眼泪从眼角流出来。可那样如常的母亲转眼就没有了,她转动轮椅靠近小酒店一端的窗口,窗外的风呼呼地刮,雪簌簌地落地,母亲将脸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用食指戳着凝结的冰花,像个看稀奇的孩子。
那样的母亲陌生遥远,好像已经同外面白茫茫的一片融为一体,雍青已经找不见她了。
忙碌的婚礼结束后,夜里回去的路不远,新郎还是怕她累,背着雍青走了很远。雍青趴在男人坚实的背上,同他说起来母亲和惠修的事情,眼泪竟然也跟着吧嗒吧嗒落了下来。新郎慌了,放她下来,拥她在怀里,笨手笨脚地安慰她。
雍青只是哭,她啜泣着靠着他的胸膛,听着他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慢慢安静了下来。路灯下的风雪染上淡淡的橘色,雍青仰起脸来,雪花飘飘洒洒落在她的肩上、发上,她恍恍惚惚觉得,那些沾上雪花的地方似乎开始发烫泛红,慢慢地要裂出一道口子来。
“你知道飞蛾吗?”
她突发奇想问新郎,却收到新郎一个疑惑的表情。
“我就是一只飞蛾。他们是光。你也是光。”
有些人是火光,雍青不顾一切飞过去了,会疼,会伤。有些人是灯泡,雍青与她永远也无法真正的相互理解,相互靠近。
雍青想着,脸上泛起微笑了。过往亲人之间的那些龃龉和不合适恋人的那些情事在心底蠢蠢欲动,它们似乎都化成黑色的飞蛾,纷纷扇动着翅膀,从雍青身体黑黝黝的空洞里飞出去,扑棱棱地飞向冰雪的世界里,消失不见了。
还好她遇上了总为她亮起的光。是属于她的光。
猜你喜欢 小姨母亲 给葡萄幼儿教育·父母孩子版(2019年3期)2019-06-22小姨的西伯利亚意林·少年版(2018年10期)2018-05-30未卜先知少年文艺·开心阅读作文(2017年10期)2017-10-26今天是母亲的生日六盘山(2016年5期)2016-11-23悲惨世界疯狂英语·阅读版(2013年2期)2013-03-22送给母亲的贴心好礼数位时尚·环球生活(2009年5期)2009-05-21母亲的养生谚饮食科学(2009年1期)2009-03-27推荐访问:飞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