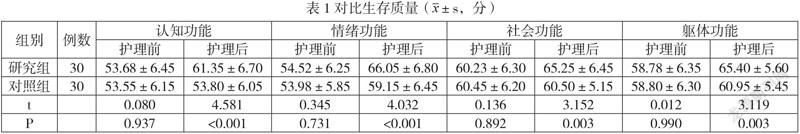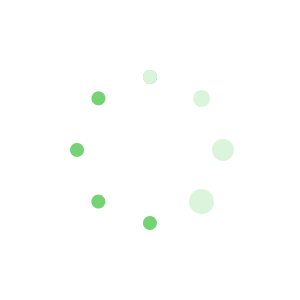一
那时我们家的理发店还没安上空调,到了夏天,只有一个破风扇在头顶“呜呜”地转着,搞不好还会把地上扫成一堆的头发再次吹飞。
我不止一次向父亲提议—买个空调吧,买个凉快的空调吧,空调摆在店里又洋气又实用。而父亲是怎么回答我的呢?他不说话,只是抬头望一眼头顶嗡嗡转着的破电扇,又低下头去忙手边的活儿。
每当这时,我就会感到从头顶蔓延到脚趾的窒息感。我会找个安静的地方给母亲打电话,说我不要住在这里了,要母亲接我回去。
父亲很少发出什么声响,就像那台破风扇,只有在干活儿的时候才会有点儿响动。他沉默地给客人理发,沉默地打扫店面,沉默地迎接一天又送走一天。正是这种沉默,让我在与他相处时,脑子里总是循环着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有一个不爱与人沟通、几乎是半个哑巴的父亲,显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我笃定父母离异是因为他的冷漠与沉寂,甚至一度庆幸自己被判给了母亲。童年里的父亲,只是汇款单上“徐尤志”这三个单薄的汉字,我无法从这里获得任何拥有父亲的体验。
平日里,我同母亲住在一起,每当放寒暑假时,母亲的手机便会收到一条来自“徐尤志”的短信。
“放假让小风来这里住几天吧。”
而母亲的脸色总会变了又变,然后望着我:“你想去吗?”
“无所谓。”我总是这么回答。
然后母亲会叹口气,起身去给我收拾行李。
去陪一个沉闷无趣的父亲,还要远离市区的朋友和电玩城,我当然不乐意。但是我还是会去的,我无法拒绝。因为这是徐尤志对他儿子仅有的要求,或者说是请求—求我去他那里住几天。
二
2路公交车经过父亲的理发店所在的街口,我背着书包下车,便能看到站台旁父亲的身影。父亲很高,这点我随他,刚上初二身高便将近1.8米。让我引以为傲的身高和长腿来自眼前这个沉默寡言到近乎木讷的男人,这怎么想都是一件神奇到有点儿不可思议的事情。
跟随父亲走回理发店的这一路是他话最多的时候,就好像他把攒了半年的话题都用在了这段路上。我努力应和他,试图跟上他的思路—父亲的思维很跳脱,上一个话题与下一个话题风马牛不相及,我在话题与话题间疲于奔命。
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父亲就像一个没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急急忙忙背完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后,便只能手足无措地僵立在舞台上,等着落幕。
而我就是那块幕布,我急于落下,遮住父子间的尴尬。
“我上楼了。”这是我在尴尬的沉默中唯一能做的选择。我几乎是仓皇地离开父亲,然后开始质疑自己来这里的理由。
从楼梯上往下望,能瞧见父亲坐在柜台里的身影,个子那么高的男人坐在柜台后,竟像是蜷在角落里,幾乎要与深灰色的墙壁融为一体。
大学时室友曾向我抱怨过他与父亲紧张的关系,但我并不能理解室友口中的“激烈争执与冲突”,因为我的父亲能与我正常地交谈已是破天荒,又何来争执一说?
我的少年时代从未给父亲留下一席之地,徐尤志对我而言,只是一个不会发出声音、快被我遗忘的一直蜷在角落里的配角。他只是一个每逢寒暑假会邀请我去小住一段时间的男人,而这仅有的相见也只是例行公事。
我也从未想过去深入了解这个配角,我觉得这无关痛痒。日子不会因为这些变得更好,也不会因此变坏。
三
在我大二的时候,我第一次收到父亲的短信,他告诉我祖父去世的消息,问我能否请假回家参加葬礼。
我说我知道了。放下电话,我才猛然惊觉自己并无泪意。从小到大,我见父亲的次数寥寥可数,见到祖父的次数更是掰着指头能数过来,我已经不大能回想起祖父的容貌,现在回想,竟是一片茫然。
我突然有些惶恐—许多年以后,当我有了白发,我回忆自己的父亲,会不会也像今天回忆祖父一般,只觉一片大雾弥漫?
坐了一天高铁,我的双脚在傍晚时分才踏上村口的土地。这种感觉很奇异,我明明才20岁,竟生出一种阔别之感。实际上,也称得上是“阔别”,自我上了小学,便再未踏足过这片土地。
这是我离开后,第一次回来。
来参加祖父的葬礼。
看到父亲时我愣了一 下,他不再是记忆里那个虽木讷但身姿挺拔的徐尤志了,我可以看见他头顶上黑白掺杂的头发。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比父亲高了半个头。
“徐风。”父亲把我领到棺旁,“给你祖父道个别。”
我安安静静地跪在垫子上叩首,然后站起来。
时近傍晚,我和父亲坐在地毯上,父亲把蜡烛芯挑亮,放在我面前。蜡烛熏人,我刚一眯眼,父亲又不动声色地把蜡烛移远了些。
“还记得你祖父长什么样子吗?”父亲突然开口,声音很轻,我甚至觉得还没有烛花爆裂的声音大。
但我听清了。
“很瘦,矮矮的,胡子特别长。”我回答。
父亲深吸了一口气,慢慢说道:“不对,你祖父特别高,身上有把子力气,一天能赶几十里路。”
“但你说的也没错。”父亲摸了摸鼻尖,“你说的是七八十岁的他,我说的是三四十岁的他。”
我眨眨眼,没说话。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打开了话匣子,但我这次愿意做一个真心实意的倾听者。
“那时候家里有你大伯和你姑,我是老二。”父亲注视着棺身被抛光的漆面,烛火在父亲眼里跳动,“每回你爷从镇上卖完肉回来,总会带几毛钱的糖,然后分给三个孩子。
“糖数不一定,有时能正好分完,有时会余出来几颗。每当这时,你爷就会说,这回多出来的糖给老大,老大带你们最辛苦;
下一次多出来糖,就分给老幺,因为老幺最小,做哥哥的得让着。”
父亲少见地笑了一下:“最后分来分去,老二从来没有分到过多余的糖。”
我有些恍惚。父亲坐在毯子上,半身被烛光照亮,半身没于黑暗。眼前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在40多年前,曾因为糖块儿的分配不均而怄气,并且一直记到了现在。
“三个孩子,数我最不听话。犯了错,你爷打半天,末了问一句知道错了没,我还一直死犟着不说话。你奶奶指着鼻尖骂我,说我生来就是跟自己老子作对的,打半天骂半天,连个声响儿都没有。
“这么多年了,你爷老了,我是在炕边儿照顾他最少的一个。”父亲嗓子里好像混进了沙砾,哑得怕人,也无力得怕人,“没当成个好儿子,当然,也没当成个好父亲。”
我喉头耸动,只觉得蜡烛离我太近了,烟气熏得我眼眶酸痛。
话很简短,但我从中得知,沉默寡言的父亲也曾是一个因为糖块儿而耿耿于怀的小孩儿,也曾在挨打时和我一样咬紧牙死不认错,也和我一样,自认为不算一个好儿子。
那个一直蜷在柜台后、几乎与墙壁融为一体的男人,我分明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和徐尤志的相似之处不再令我惊奇,因为本该如此。
汇款单上“徐尤志”三个字突然生出骨架,长出血与肉,站立起来,心脏开始跳动,脉搏带来温度。我看到时光飞逝,将那个争着要糖块儿的小孩儿拔高到成人模样,再给他染上风霜,刻下痕迹。
我恍惚间开始明白,自己在这20年间都错过了什么。我从未试图和父亲沟通过,是我亲手将父亲变成了单薄的汇款单上的名字。我无视他每一次试图与我沟通的努力,忽略他的挣扎,脑子里只想着逃避尴尬。
那夜我和父亲坐在地上,坐了很久。
我将头埋在膝盖间。思绪纷乱,困意又使我昏昏沉沉。肩头被父亲披上外套,我听见父亲在我耳边悄声道:“店里安空调了,暑假来住几天好吗?”
我抬起头,缓慢道:“好。”
一直蜷缩在角落里、被我错过多年的配角嘶吼着发出声音,终于被我听见。我看着他生出血肉,朝我走来。而我终于开始了解他的过去,经历他所经历的。
猜你喜欢 块儿汇款单角落里 分饼的学问意林·少年版(2021年2期)2021-02-22父亲的汇款单青年文学家(2020年22期)2020-08-31雨和伞新作文·小学低年级版(2019年8期)2019-09-25雨和伞故事作文·高年级(2019年8期)2019-08-20取款遭遇记侨园(2019年4期)2019-04-28画春风扬子江(2019年1期)2019-03-08汇款单被冒领邮局应担责中老年健康(2017年8期)2017-12-16天生的本领学苑创造·A版(2017年9期)2017-09-25马铃薯的魔法红领巾·萌芽(2017年6期)2017-07-08饭补意林(2016年11期)2016-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