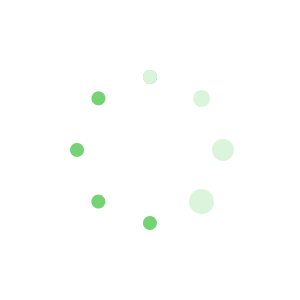王陌书
我搭乘一叶扁舟,既没有张帆,也没有划桨,躺在甲板上顺流而下。蒲苇如时间涌动,舔舐着我内心的边界线。船头空了的酒壶压着几张写满草书的黄麻纸,那潦草的字迹均出自我手,此外还有一根没点燃的白蜡烛。我头枕着手,还没有想到要在何处泊船。
经过蒲苇丛,旁边的枝条摸索着我的侧面,但没有叵测的企图,我也顺其自然地折下其中发芽的一枝。远处受惊的几只鹭鸟振翅起飞,忽高忽低,沦为了几个斑驳的虚点。茫茫如雪的白絮误认了天与地,往弧形的天穹飘落,似乎正是它们汇聚起轻浮的云朵。它们放荡不羁,比青楼女子更容易委身于人,也更容易弃之而去,留下原地的相思者。刚才还偎依着我的胸膛,顷刻便随风而散去寻找新欢,伸手亦无法挽留。
随着蒲苇稀疏起来,视野渐渐开阔,船从沼泽驶入河道。我感觉自己随时会化作鹤遨游于天地之间,不受拘束,散落片片轻得可以飘浮的羽毛。如此风光让我忘记了正值明亡之季,直到看见浸泡得肿胀的尸体从船的侧畔漂过,那难以辨别的面容仍流露着不甘,才意识到即便逃避纷乱,纷乱也终究会找来。我忽然宁愿化作一棵树,看不见一切,没有悲欢。
我的目光为河岸边缘挂着一串破旧白灯笼的木杆所吸引,那四周扎立着几个草人,堆积了几处乱石。若非读过史书的相关记载,不能相信那一带是万人冢,为隋炀帝修运河的民夫们的乱葬岗。像这样的前朝往事总是惹人伤怀,下江都的炀帝被宇文化及所弑,他的天下旋即变为各路诸侯厮杀的修罗场。而这些被驱使的百姓,因为他的一个念头死在异乡,累累白骨已经腐朽,归于尘土,修的永济渠也早已因淤塞而废弃,干枯的河床长满草木。没有留下古迹,也就没有哪朝的诗人特意来此叹息他们的往事。只有一些终日劳作的黔首,会唱起关于他们死后当地有怨灵作祟的歌谣。
曾经一位故人跟我说过,神鬼之说不可尽信。泥塑的菩萨倘若有灵自不会忍心见世人受苦,然而众生皆苦,要么是不愿普度世人,要么是不能。而倘若含恨而终的冤魂真能索命,那为何史上善终的恶人又如此之多?以功在杀人多而封侯拜将者不可胜数,都说因果报应,该应验却未应验的时候太多。
他所言在理,当时我也没有任何辩驳,点头称是。然而后来他自己却遁入空门,剃发为僧,终日诵经。我问他是何故,他答曰,即便没有佛,也要造出一座佛来,不为虚无缥缈的来生,只是为了今生有所宽慰和寄托。而看着他敲响木鱼的我站在门槛外无言以答。
前方不远的柳树旁有一人头顶竹笠,右手握着无鞘的剑,左手拎着用布巾包裹的一物站在河畔,看上去绝非善类,连下垂的柳丝也不敢触及他。隔着很远就被他尖锐的目光刺伤,他丝毫不介意靴子略微浸没在水中,隔着波光粼粼的河面向我喊话:“船家,现下往哪里去?”
我略微起身:“往博陵去。”
他说:“给你三吊铜钱,可否载我去碚州?”
我说:“尊驾去那作甚。”
他说:“去碚州买盐。”
我说:“尊驾姓甚?籍贯何处?最近于哪谋事?”
他说:“姓何,名保大。凤阳府人。最近在开封谋事。”
于是我不再多问,扎下竹篙把木船停住,让他径直跃上船来。随着摇晃渐渐停歇,他扔下三吊铜钱,放下布巾包裹之物盘腿而坐。我收起沉甸甸的铜钱,将船继续往下游推去。没过多久我看见披甲的几人骑马赶至他上船的河畔,驱马涉水到马不肯往前的深水地带,他们剃了头梳着金钱鼠尾的辫子,跳下马拔出刀劈砍旁边的芦苇秆,朝我呼喊或者呵斥,相隔太远已经听不见说什么了。
走水路去碚州只需要半日,从那里再去博陵则需要一日,起伏的路上我升起帆,然后坐在船尾剥莲蓬。他看见我写的字,缓缓开口:“阁下是读书人?写的可是:
长夜渐凝半廓天,樵者别梦此丘枫,
颓云倾碎琉璃散,眠火独吟弱水轻,
远影澹澹岛上波,昏晓渺渺故人踪,
无所依兮无所凭,四翼皆托浮生中。
我说:“自娱之作,不必当真。”
他说:“虽然不算上乘之作,不过颇有意境,可惜过于颓丧了。”
我说:“打油诗罢了,尊驾说是便是。”
他说:“不愿多谈这些也罢,不知这一带水路是否太平?”
我说:“这一带水路,渔民们平时打鱼、采莲、编蒲苇席,在此之余待有大船经过,便取出鱼叉刀枪做起水匪,杀人越货再把船凿沉。不过像我这种小舟他们是不放在眼里的,除了当柴火外没别的用处。”
他说:“世风日下,早些年还不至于此。”
我说:“盐铁历代以来皆为官卖,淮北的盐贩到淮南价格高二十倍,可谓暴利。太平年景贩私盐可是杀头的重罪,家属也要流放琼州,即便如此私盐贩子也是前赴后继。更何况现在天下已乱,流寇四起,鞑子也已经入关,没有官盐只有私盐在售,正是做这种营生的好时机,尊驾可是有意于此乎?”
他说:“正是,我此去碚州正是买盐。”
我说:“但是碚州并不产盐,产盐的是旁边的淅川,尊驾方才怕是在诓我吧?想必尊驾不姓何,也不在开封做事。尊驾不肯谈及自己,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河岸上的几人追之未及,恐怕也不会善罢甘休,想必会快马骑去碚州守候……而他们追你,估计也是为你手中之物……”
终于,他回过头来摘下斗笠露出消瘦冷峻的面孔,额头上有道疤痕,一对女人般的耳朵被鬓角的头发覆盖。他将剑钉在船板上:“船家,如此有心打探我的事情,不怕死吗?还是闭嘴等我上岸好去受用那几吊铜钱吧。”
我说:“尊驾觉得自己的命只值三吊钱?”
他说:“你是何意?”
我说:“尊驾一副亡命之徒的模样,身后又有追兵,定是涉及什么血案。尊驾可能为了不泄露行踪,等到碚州上岸时便将我灭口,以免之后有什么麻烦。而那几个追兵,可能誤以为我是尊驾的同谋,而追寻我以便拷问你的下落。区区三吊钱,可不值得在下以身犯险。”
他说:“阁下绝非靠摇橹过活的艄夫,究竟是何人?”
我说:“艄夫罢了,专送此岸之客往彼岸去。”
他说:“阁下信佛?此岸和彼岸,对我来说太玄奥了。”
我说:“不信,也未曾受戒。”
他警惕起来握紧剑说:“那阁下想拿我去见官不成?”
我的笑沿着竹竿化作荡漾的水花,我说:“官?哪个官?天下已乱,几年前这一带的官是明廷派的,过了阵又是闯王派的,现在则是满清派的,谁知道等明天又会是谁呢?我从不过问别人的仇怨。”
他说:“那阁下此番究竟为何?”
我说:“救人而已,我曾经起誓无论看到何人受困岸边向我呼喊,书生也好屠夫也好官宦也好娼妓也好盗贼也好,我皆会让其上船。”
他对此嗤之以鼻:“真是菩萨心肠。”同时解开布巾,里面是一颗头发散乱的人头,血污已经结痂,闭目的神情极其安详。几乎光秃秃的头顶,只有一条仅可穿过铜钱眼的辫子。他继续说:“此乃恶人,为满洲镶白旗佐领,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追数日方才斩下其首级,那些追我的人就是他部下。方才倘若是我追他至岸边,他朝你呼救,你亦渡他吗?”
我说:“当然,不论是谁。”
他说:“善恶不分。”
我说:“善恶难以分清。”
他说:“我本名鲁能奇,北直隶正定人。此行去碚州,乃因不愿剃头想从那去西南投奔晋王李定国,难道他如今匡扶明室,抗击北虏不是仁善吗?你若有志为苍生考虑可随我一同拜见,我想晋王定会委赏识于你。”
我说:“清兵杀人,晋王亦杀人,多寡而已。他义父西王在时被明廷视为流寇屡屡发大兵征剿,后来西王割据川蜀,川蜀几乎到了人口十不存一的地步,百姓谓之为活阎罗,在其手下做事手会干净没有染血么?今满清势大又杀了他义父,故晋王能和明廷协力抗虏,双方实则同床异梦,他日若能北伐直捣燕京,他怕也是会效仿刘裕之故事的吧。”
他说:“酸儒之见。你满腹韬略,却甘愿隐于这江河之间,任由这天下如此骚乱下去吗?欲成大事者伤春悲秋,哀花怜草,势必一事无成。”
我说:“时势非人力可强求,诸葛亮出草庐数十载,至五丈原身死也未能使九州重归于汉室,他哪怕续命再七出祁山,也注定徒劳无功,徒然加重蜀中百姓困苦而已。很多时候做得越多错得越多,做得越少错得越少,而什么都不做也就什么都不会错。我不信天命,可我信时势。”
他说:“敢问当今的时势如何?”
我说:“清廷已得中原,方兴未艾,而其他几路势力或偏居东南,或残存于西南,边角之地,难成撼动天下的气候。何况清廷一心,汉人却有几心,内部掣肘太甚。对百姓而言脑袋只有一个,清兵割只需一刀,明兵割亦只需要一刀,还是期盼仗早点打完吧。”
他说:“懦夫尔。”
我说:“天生万物,各行其是。”
他说:“也罢,人各有志,我不强求。”
话不投机,随后我们二人无话,潺潺的河水渗入彼此的裂隙,滋长无形的荒草。我早已经适应了微幅的摇晃,偶尔到了岸上反而不适,肉身认定这个世界像淋雨后打寒战的麋鹿,得不停颤抖。而木船则如潜入水中的旱獭,即便下部满是水藻也仍记得自己来自陆地,需要呼吸,终究是岸在水面的延伸。我嫌风的喘息太过微弱,降下帆再次撑动竹竿不停搅碎水面的倒影,变化出的各种光影褶皱很快归于原状,丝毫没有留下船驶过的痕迹。
等船到碚州地界已是黄昏,血色的落日在远处的水面溶解,变为一摊破碎的夕阳覆盖摇曳的蒲苇。包括我的面孔在内的一切都开始渐渐黯淡,褪去白昼的外壳,长出黑夜的鳞片。时辰的分界点极其模糊,所以人总以为它是没有真正区别昼夜的一刻,因为它们都会提前渗透进对方的身体。鲁能奇看到一处盖有土地庙的缓坡,叫我在河畔停船,那庙宇不过人高,缀连的瓦片缝隙长满蒲公英,里面的神像已经失踪,怕是被饥民拿去铸铜钱了吧。他留下一颗银纽扣,拎着人头跃上岸去,头也不回:“告辞,以后若改主意,用这个来西南找我吧。”
我身体倾斜,倚靠竹竿:“告辞,他日再会。”
他跟我都知道,此生是不会第二次相遇的。
望着他的身影湮没在被树木倾轧得快消失的羊肠小道上,我知道我也得找個地方泊船过夜了,于是用力划船往别处去。每次扎下光滑瘦长的竹竿,都可以测量出那里的水有多深,深浅对我来说决定划船是否吃力。尽管如此,我对于水还是感到一种隔阂,每次把头扎进水下凝视浮草最终呛到水都会加深这种感觉。
我决定在一片长满大薸的浅滩泊船,通过岸边的蚂蚁,可以知道夜里不会有暴风雨,也就是说我可以不必担心自然的危险,只需要担心人的危险。船头碰到大薸的叶子发出怪异的声音,当船停下以后,如刀的船几乎把绿色的浅滩剖成两半,那些断裂的茎叶需要很久才能愈合。或许,下面的鱼仰视落叶状的船底,只会认为是一条大鱼在游弋觅食吧。
天色变暗,我点上纱布灯笼,然后开始钓鱼。先用空钩钓起一尾小鱼,再以小鱼作饵料钓起一尾大鱼,我将其甩到船板上,它不断弹跳想要挣扎,我并没有阻止,等着它筋疲力尽。它是一条鲻鱼,我找来匕首料理完以后,扔进船上的锅里煮汤,掏出香料锦囊往沸腾的汤里面倒了些许茴香碎屑。我观察火苗如何蹿动,每次眨眼都有感觉错过了什么的幻觉,也就是这时,我又想起了那位落发为僧的故人,在他出家以前我们曾一起钓鱼。
那时我们还是不识愁滋味的纨绔子弟,生于江南官宦豪门,却无意入仕,好楼阁,好美婢,好骏马,好花鸟,好书画……纸醉金迷,未曾想过有朝一日家破人亡,亲族离散。那是炎热的三伏天,我跟他坐在岸边的柳荫下面,旁边两个束羊角辫的僮仆为我们摇着扇子,可还是很热。我头顶的镂金冠上盖着反过来的荷叶,握住钓竿的手迟迟没有察觉下坠的沉重。我们经常打赌,那次赌谁先钓到鱼,赌注是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
最终是他先钓起了一尾鲤鱼,随后就把它放回水中,这是他的习惯,他认为钓鱼只是游戏不必杀生。他告诉我那尾鱼的唇上有两个勾洞,另一个勾洞是他以前留下的,他钓起了它两次,也算是一种缘分。而我不以为然,继续等自己的鱼竿剧烈晃动的一刻,但是那天我始终没有等到。
断断续续的箫声打乱了回忆,那从一片桃树后传来,声调极其哀怨,我知道曲名是《闺怨》,宋代落榜生假托怨妇所作,抒发不得志之意。我以前常听此调,在秦淮河畔的青楼上,被鸨母调教好的瘦马依偎着我不停劝酒。迷醉之间听见隔间传来此曲,多是落榜的贡生们聚在一起让乐工吹奏,他们专爱这首曲子。而我并不喜欢,觉得那少了淡泊之志,当然,我有世袭的爵禄才能如此看淡,若是生于寒门恐怕也不能免俗的吧。想到这里,我用一把沙子熄灭掉炉火,再将船往桃树林划去,隐约可以瞧见火焰悬浮于幽暗间。桃树的枝丫互相交错,因为不是花开的时节,少了片片飘零的绯红,我也就没有幻想自己是在前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我想,即便真有那样遗世独立的地方存在,纯洁无瑕定是妄谈,那必然是长期近亲婚配的诡异之地。
终于,我抵近火光,看见一女子跪坐在落叶上,独自吹着长箫。她穿着淡绿色袄裙,头发上没有首饰,面孔也未施脂粉。她下半身的裙褶湿漉漉的,沾着水藻的残片,姣好的容貌在火光烘托下,因悲伤而显现的蹙眉也颇有气质,在我看来她犹如落入污泥的莲花。奇怪的是她听见船来的声响,并未逃避,读过许多志异怪谈的我自然想到鬼魅,可我并非进京赶考或落榜归乡的书生,也无期盼女鬼垂青的痴念,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我不等停靠,在船上作揖:“请娘子勿惊,我非匪类,江上一识得字的艄夫耳,因听娘子箫声为《闺怨》,乃寻至此,如白居易欲见琵琶女之故。”
她没有丝毫的慌张,起身答礼:“先生亦通音律?”
我说:“粗通而已,我曾流连南京的朝夕阁,常听乐妓吹奏,不过我不喜欢此曲,我喜欢的是《瑞鹧鸪》,有时自己也会下场即兴弹奏。”
她叹了口气又吹奏起来,悠扬的曲调毫无间隙,如木楔一点点透进我海绵般的体内,她吹奏的正是《瑞鹧鸪》。往昔的场景像折扇缓缓展开,我立刻将其收拢,不想再有徒增伤感的回忆。我说:“虽然没有箜篌、琵琶、古筝这些乐器配合,未能尽善尽美,可技艺也臻于极致,我自愧弗如。”
她略微低头:“先生赏识,贱妾不胜惶恐。”
我说:“娘子为何流落于此荒外之地?如今匪患横行,孤身在外很容易遭遇不测。不知要往何处去,若有烦忧,我定略尽绵薄之力。”
她说:“不敢劳累先生。”
我说:“但说无妨。”
几番推脱之后,她咬住下唇,有些吞吐地说道:“贱妾名唤柳七娘,七岁上就被父亲卖去淮州做瘦马,习得书画舞乐,十五及笄后成了轻霜楼的头牌。欢场之事,先生应该熟悉,男的为色女的为利,觥筹交错之间全无真情实意,故而我有从良之志。去年腊月间,结识一位周姓公子,他虽落魄,却饱读诗书,待我体贴,不似那些朱门子弟。贱妾觉得可以将终生托付于他,便将多年私藏下来的银两交给他,让他为我赎身,余下来的银两他用来赶考也好用来做买卖也好,都可保我二人今后的衣食。但是……”
她一阵哽咽,竟说不出话来,我不顾鱼汤渐凉说:“后来如何?”我已经料想到那周姓公子辜负了她,从前在国子监读书,私下读些老师斥责为伤风败俗的杂书,常在冯梦龙之流编写的小说中见这样的故事,薄情郎和痴情女最终没有好归宿的套路,然而还是这样问。
她取出绣花手帕拭泪:“贱妾命苦……后来让他带我归乡,他却找借口百般推脱,说我不懂纺织这些生计,归乡也难以维生,倒不如在淮州从长计议。我知道他心里觉得娶妓回家并不光彩,有辱门风,让他难以在宗族内立足。就这样一拖再拖,到了近日他突然答应,雇了一辆马车跟我上路。不承想……”
我对这种停顿产生了自己都难以察觉的不快:“不承想如何?”
她说:“行至这江边无人之处,他竟露出凶相,使蛮力夺去贱妾的首饰,将我抛弃在这荒外,任我为豺狼之食。对此负心人贱妾肝肠寸断,本不欲生,想要投水自尽,奈何终究是一怯懦弱女子,至水没腰处而返。”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你还可有哪里可投奔吗?我送你去。”
她说:“贱妾已不知何去何从。”
我说:“难道宁愿在这化作无人收尸的骸骨?”
她说:“不愿,那般死了会不得超生。”
我说:“那就再想想,莫为负心人寻死觅活。”
迟疑片刻之后,她说:“回淮州尚可维生。”
我说:“此去淮州需要一日,看来得就此改道了,你上船吧,我送你去淮州渡口。”
她说:“贱妾已身无分文,先生恩德,无以为报。”
我说:“不足介怀,劳烦娘子上船。”
收起长箫,她拨去膝上黏着的落叶,踉踉跄跄地踩着优雅的碎步,衣裙的边角宛若摇摆的蝴蝶,呈现近乎纷飞的景象。她不敢跨大步,因此到船前得由我拉她一把。我预先想她很是轻飘,可未曾想她是那样轻飘,故而我隔着衣袖握住她的手,没有拿捏好力度,她一下子倾倒向我胸前,不是她——而是我马上由于羞怯而后退躲避,她因此双膝并拢瘫坐在船上。她的身体很冷,肌肤接触的瞬间我以为自己碰到了冰,视线的边缘似乎泛起雪屑,身体的关节仿佛冻结,我感觉自己不是让一个女人上船,而是让一个冬天上船。再过不久,我害怕小舟的周围水面凝固,让我进退不能。
幽暗的桃林默不作声地目视小船离去,它在水中的倒影很是憔悴,狭長的苍白枝条把夜撕成碎片,再按原样重新拼凑起来,只是几颗星星摆错了位置,除我以外无人察觉。她披散黑发坐在旁边,落寞的神情惹人怜惜,我并非没有发现异样,可早已经发誓无论是谁欲坐我的船去彼岸,我都得送其前往。她瀑布般的长发快要浸入水中,我想要提醒她,却始终开不了口。我曾经也放浪形骸,和酒肉朋友夜夜笙歌,以至于昼与夜颠倒过来。在欢场也曾见过比她更出众的女子,但总觉得她身上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却又无法形容。
我觉得越来越冷,嘴唇开始乌紫,必须想办法取暖,我想到船头置放的白色蜡烛,我找来火折子几次点燃它。可它又几次被风熄灭,于是索性不点,轻烟很快飘散。她说:“先生可是觉得冷?”
我说:“等风停了便好。”
她说:“先生这般精通音律,想也是官宦子弟,现今孤身一人?未有家室?”
我说:“孑然一身,逍遥自在,官宦子弟是以前的事了,现在门庭败落,不过一介草民。哪怕是昔日皇帝也要让三分的王谢大族,也终究免不了潦倒,何况随一朝代起的贵胄,势必也随一朝代倾颓。命也。”
她说:“若是先生不嫌弃……救命之恩,我当……”
預料到她接下去要说什么,我明知故问:“回到淮州,你以何谋生?”
她低下头:“回到淮州,怕只能跟妈妈再签一张卖身契纸了。”
我故意说:“虽然这么说有些伤人,那些恩客虽无真心,可是愿意一掷千金只为博美人一笑,毫不吝啬,不似那等负心汉,无真心还谋夺你的钱财。世上的男人分为两种,有钱的薄情郎和没钱的薄情郎,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差。”
她提醒我:“可先生亦是……男人。”
我故意说:“不错,我年少时也很薄情,结识过许多才貌出众的女子,为她们花钱太多导致家父几乎想逐我出门,可到了现在,我却无法将她们的样貌和名字在记忆中对号,总出差错。我从不自称多情去辜负别人,只为及时行乐,从无任何承诺。”
她怏怏不乐:“受教。”
我故意说:“不过——你现在正值青春年华,他们自然宠你,可以衣食无忧可以涂脂抹粉,可待到年老色衰又当如何?被人冷落,新人歌舞时只能在角落里吹奏长箫,运气好嫁给某人做妾受尽正妻白眼,运气坏……”
她闭上眼睛:“风尘女子,命当如此。”
我叹了一口气,未再多说其他,说这番故意的刻薄之言,是为了在她和我之间构筑一道隔阂的堤坝。我的双眼可以洞悉他人的宿命,可是很多时候知道依然无可奈何,犹如瞧见阴霾天空下群鸟低旋可以预见将有暴雨,然而暴雨不会因为人有所预见而得以避免,所以对自身尚且无能为力的我总是假装不知道。她再度吹起了长箫,这次是我未曾听闻的曲调,更令人诧异的是船驶过的余波底下,一群游鱼竟尾随而来,漾起不规则的涟漪。箫声淌入脑海以悲怆的边际概括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她是为现在而奏,描述素昧平生的她和我——她对救了她的我心存遐想,情愫难以言表。我亦心存渴慕,却又故作冷漠姿态。她和我都知道对方的心思,却都不可能首先越界,欺骗自己并无他想。不过箫声中那片桃林开满桃花,飘落的花瓣让夜空变为绯色,仿佛一切只是桃树的梦。
困倦感化作密集的鱼群袭来,和黎明之间相距一场长眠,被轻易压垮的我昏昏欲睡,已经开始觉得手指由于寒冷而失去了知觉。或许,我已经睡着了只不过自己没有发觉,证据是我的手中竟攥着一瓣桃花。身体渐渐渗出冷汗,如果我已经入眠,那究竟从何时开始的呢?黄昏听见箫声以后,清晨喝光一壶酒以后,还是我出生发出啼哭以后?往事如烟,乘舟漂泊于江河数载,如今我却不能够追溯到确信自己处在现实的那一刻。
躺卧在船板上仰视那盏灯,我犹如倒下的桦树动弹不得,对一切的反应都异常迟缓。胸前的交领被解开,柔软而温暖的形状匍匐在上面,是她的躯体,她的长发垂到我的面颊。她说:“还觉得冷吗?”
我说:“我记得你的身体冷极了,不可能如此炽热。”
她朝我的眼睛呵了口气,似乎想化开表面的冰霜一般:“你记错了,回答我你现在还觉得冷吗?”
我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为何如此?”
她的指尖停在锁骨与肩胛骨之间:“因为你渴慕我。”
我说:“确实如此,可渴慕并不意味着我得去占有。”
她的绸裙发出躁动的悉瑟:“什么意思?”
我说:“我不会摘下所有喜欢的花,也不会去毁掉所有讨厌的书,我不会感情用事。欣赏的人远远地欣赏就好,有一个理由让我渴望占有你,可有无数个理由阻止我的渴望。”
她的耳朵抵住我的面颊:“我不想听,解开我的裙带,我让你暖和。”
我说:“我做不到。”
她的一根睫毛飘落到我眼睑内,引起刺痛:“你在顾忌什么?”
我说:“并不是说顾忌什么,我不信鬼神,原则上无所顾忌。可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你热情并怀有憧憬,我冷漠且毫无期待,我们的命运不应该有这样的交集,我不愿这种有些庸俗,有些诡异,有些放荡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的泪水顺着我的下颌流淌:“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合为一体,消除掉所有的差异吧。”她突然笑了,凄迷而且狡黠的笑容如有毒的花绽放。接下来我们裸露的部分粘结在一起,并非淫秽的隐喻,而是我们仿佛两根挨着一起燃烧的蜡烛,因为熔化而纠缠在一起,逐渐难以分清彼此,说不清是谁在熔化谁。我的手和她的手在混合,由于恐惧想要挣扎,可像陷入沼泽般陷入她柔软而且潮湿的躯壳内,沉溺其中,我的耳朵长出枝叶,她的指尖隆起桃花的花骨朵,我们正在渐渐变成桃树。
我发出惊悚的嘶叫,睁开眼睛看见被交错的树枝分割的灰蒙蒙天空,感觉从噩梦中惊醒。眼前的一切告诉我已经是清晨了,我认得前方有石狮子的拱桥,这里是淮州渡口。我环顾四周不见她的踪影,暧昧的梦魇仿佛没有发生过,我的身上没有残留她丝毫的气息,像洗衣裳时一般拧转几下就会渗水的潮湿空气飘荡在四周,我的迷惘混在雾中,以至于辨别不出来。那只是一场迷梦吗?可我的手中又确实攥着一瓣桃花。
或许,周生遗弃她以后她便投水而亡,由于对生的眷恋鬼魂回到岸上的篝火边吹箫,她没有发觉自己已经溺死。当我的小舟把她载回淮州,她最后的残念消散,于是她也就消散了。虽然不信鬼神,可我只能如此解释,因为我更不愿相信这是一场自身欲念衍生的迷梦。
无法形容的沮丧感包裹着我,由于不想记住所以松开手,让那一瓣桃花在婉转的飘零后沉于遗忘,我想,若真有阴间的话亡魂也并不可怕,那终究是更单纯的人,凭借死前关于爱或恨的些许念想游荡人间。我将船往河央划去,然后随波逐流,任其在雾中前行。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人在呼唤我,他说:“船家,船家。”
隔着大雾,我并不想答应,蹲在船边将头浸到水下让自己尽快清醒。睁眼凝视流动的一切,不论是水草还是卵石都变得弯曲,终日以水为邻的我到底还是无法理解水。当抬头猛烈呼吸的时候,我看见雾中的人影逐渐显现出来,一开始也是弯曲的。那人和我年纪相仿,他说:“船家,怎么不答应?”
我拨撩湿漉漉的头发:“因为不想答应。”
他說:“这话颇为实在,也不似别的船家那般油滑。不管你愿不愿意做这门生意,我还是要问,给你五十文能否送我到鹈鹕泽?”
我说:“尊驾去那作甚?”
他说:“莫问。”
我说:“尊驾姓甚?籍贯何处?于何处谋事?”
他说:“莫问。”
我说:“那我可问尊驾何事?”
他说:“再多给你五十文,一概莫问。”
于是我便一概不问,将船靠到岸边让他上来,每次有人上船我总是会问其底细,虽然对方总是说谎随便编造来历,这是一种习惯,很少有这般实在的人。鹈鹕泽距离不远,大约半个时辰便能抵达,去那里的人通常是想见接头人去黑石寨好落草为寇。等船驶到宽阔处,我想问是否打算交我的人头——他上山落草要杀人纳投名状,但想到已经答应他一概莫问,所以始终一言不发。
前方的河湾中露出一根桅杆头,是过往飞鸟停歇的落脚点,下面有很久以前沉没的漕运船,不知为何一直没有谁去打捞。那人站在船头四处张望,目光如木梳篦过视线内的一切,似乎连一只蚱蜢都未遗漏。置身于天地山川之中,他跟我相距很近又可以说相距很远。往昔乘船的人我总是一目了然,知道其为何而来为何而去,可眼前这个人我却琢磨不透。
等船行驶过一片芦苇,他令我在水流急促的河湾停泊:“劳烦在这停上半个时辰,若半个时辰内我未回来,便可自行离去。”
环顾四周,我确信除非他变为鱼否则再无别的去处,我说:“尊驾是在说糊涂话吧,从这小舟去不了别处,得等靠岸了。”
他拔下发簪说:“不是,你勿多言。”
我把竹竿扎下:“此处水流湍急……”
他仿佛没有听见,褪下衣裤屏住呼吸一头扎进水中,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破裂的水花就已经愈合,并未留下任何的疤痕。我尽力让船在急流中停留,轻松地随波逐流以至于产生自己驯化了河流的错觉,此刻我认识到它的野性是多么桀骜不驯,即便我费尽全力船还是缓慢地漂离。我的目光在水面漂浮,看不到他的身影,心里已经做好了他葬身鱼腹的准备。
半个时辰还差半刻,一条湿漉漉的手臂攀上船沿,他还是浮了上来,另一只手中拿着锈迹斑斑的长剑,剑在冷淡的阳光下没有任何金属的光泽。他长出了鳃一般,漫长的潜水丝毫没有影响呼吸,冷静的姿态仿佛只是去洗了澡而已。他重新穿上衣裤,等系好腰带以后,他说:“我去年坐船经过此地,洗去佩剑上的血渍时不慎将其落入水中,故现在回来捞取。”
我说:“尊驾此番专为捞剑,确是稀奇之事。”
他说:“此剑虽称不上削铁如泥,可也杀人无算,古时候曾斩下过羯人侯景的脑袋,据说他的脑袋很肥硕,需要连斩两下。”
我说:“怪不得如此厚的锈迹也难以覆盖不详的寒光。”
他说:“你知我捞取此剑是为何缘故么?”
我说:“为了杀人。”
他说:“猜对了,附近可有上岁数的出色铁匠?这把剑肯定得重新淬火,方能再次尝血。”
我说:“恕我不知。”
他说:“也罢,等我从鹈鹕泽回去再慢慢找。”
我很想问他,时隔一年他如何能够从原地捞回那把剑,虽不至于说犹如大海捞针,可也相差无几。我很想问他,此番捞起剑准备先拿谁的性命试一试。可我已经答应一概莫问,随后,直至他从鹈鹕泽登岸,我们也再未有过交谈。船未停靠他便跃下,水没过膝盖也毫不在乎,他穿过一群野菖蒲没有回头。
我目送他消失于林中,我曾这样目送许多渡客去往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都突然出现再突然消失,此前和往后显得虚无缥缈。有僧人,有侠客,有盗匪,有官吏,有舞女……浮现出众生相,我的小舟连接了无数人命运中的两点,我送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从未擅自更改过航向,也就是没有更改过他们的命运。心怀执念的他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可笑的是作为艄夫的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的彼岸在哪。
都说此岸的今生痛苦,故世人皆向往彼岸的极乐世界,然而那只是对遥远的憧憬,人皆爱生疏且不可得之物。对我而言彼岸是此岸的倒影,此岸的丑恶必在彼岸浮现,彼岸亦非净土,所以我只能在没有始与终的河上漂流。
等雾彻底散去以后,我再度躺在船上随波逐流,又过了许久,恍惚之间的缝隙为我裂开了一个名为死亡的口子,透过那道众生共同的伤口,我窥见了血红色的彼岸花盛开的地方,那是黄泉路上。它们依托于荆棘,被刺伤的地方流淌出单色的彩虹,而被我遗忘的亡者踏过那里,留下孤单的不可寻觅的足迹。我沉溺于那纷繁的幻象,与此同时,远方依稀可以听见瀑布般下坠的湍流,可我仍未下定停泊的决心,渴望继续顺其自然。
责任编辑:卢 欣
推荐访问: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