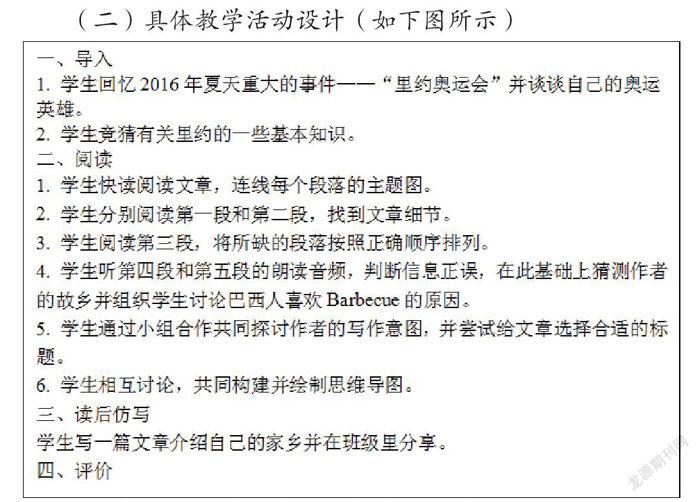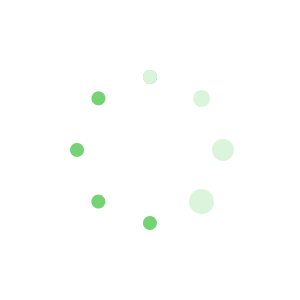摘 要:依据慈善动机,慈善被分为功利性慈善和非功利性慈善。慈善歧视客观存在于两种类型的慈善之中,并集中表现为目的性歧视、规则性歧视和选择性歧视。慈善歧视的发生受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差异这一慈善发生所需的必要条件与慈善资源的有限性是诱发慈善歧视的客观因素。从主观上看,偏见是两类慈善中出现歧视的共同可能。但不同的是,在功利性慈善之中,功利性目的的慈善追求是慈善歧视的可能诱因。而慈善行为主体从自然之中形成的选择习性、共情程度以及对慈善对象的发展性考量,则是非功利性慈善中出现慈善歧视的可能诱因。慈善歧视不仅是对慈善促进分配正义功能的背离,也以“条件准入”理念置换人人具有慈善共建权、共享权的价值原则,更存在着诱发新社会风险的可能。一方面,应强化慈善系统内部的能力建设,着力提升慈善行为主体理性抉择能力,促进其端正慈善动机,并深度延展慈善资源供给链。另一方面,也应构建出集慈善法治理、慈善伦理矫治和慈善教育引导于一体的外部治理环境,内外联动,推动慈善深度健康、全面发展。
关键词:慈善歧视;慈善治理;慈善发展
作者简介:张登皓,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性别伦理与公益慈善(E-mail:zhangdenghao151@163.com ;浙江 杭州 310058)。
基金项目:中慈联敦和·竹林计划三期资助课题“当代中国慈善的伦理风险及其规避研究”(2018ZLJH-14)。
中图分类号:C913.7 ;B8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6-0080-13
歧视及其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这一方面源于歧视自身充满着背离平等、公正的价值性向;另一方面在于歧视成为了泛化存在的社会心态和人之实践,即“在许多环境中,人们因残疾、性别、地位、态度、年龄、种族或宗教而受到歧视,”Celine Osukwu.“Disability,Performance,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Service to Humanity”,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Volume 108,2019(1)p.63.进而加剧社会不公正,阻碍社会正义的实现。在慈善中也常常出现歧视现象,这不仅偏离慈善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指向,并对慈善的良好发展造成很大危害。系统检视和反思慈善歧视,并有效探索出治理慈善歧视的实践路径是深度健全发展慈善的题中之义。
一 慈善歧视的概念释义
慈善不仅关系到理念和价值,也关系到具体行为。(美)罗伯特·L·佩顿,迈克尔·P·穆迪著,郭烁译:《慈善的意义与使命》,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13年,第11页。从价值理念来看,慈善是“善心、善举、善功的三者统一,”朱贻庭,段江波:《善心、善举、善功三者统一——论中国传统慈善伦理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22页。是一个完整的善的系统。从具体行为而言,慈善是为个体或一定群体、组织等捐赠物资、时间和提供服务的志愿活动。目前,尽管对慈善歧视这一概念尚未形成认知共识和建立清晰界定,但层见叠出的诸如对同性恋、犯人、残疾人等的慈善不公正甚至慈善无视,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市红十字会对捐赠物资的不公正分配等慈善事件,却内携着慈善歧视的基本意蕴。这为我们系统反思慈善歧视提供着事实依据。与之同时,马修·哈丁在《慈善法与自由国》一书中,确证了歧视客观存在于慈善之中,并将“以慈善法消除慈善活动中的歧视”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加以系统研讨,考辨了慈善、歧视与自主三者的内在关联,强调慈善法在治理慈善活动中的歧视现象时应注重好实践边界。这也为我们深度检视慈善歧视提供了理论线索。
具体来看,慈善歧视是歧視概念在慈善之中的应用,借以歧视表征某种或某些慈善活动。因而,释义慈善歧视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认识歧视这一概念。
当下,对歧视概念的界定存在着不同的视域论断。一是从社会心理学出发定义歧视概念,这以阿伦森、巴隆等人为主要代表。阿伦森将歧视定义为“对特定团体成员的不公平、负面或者伤害性的行为”(美)阿伦森等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第5版),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90页。;巴隆、布兰斯科姆以及伯恩等人则把歧视视为偏见的行为表现。(美)巴隆,布兰斯科姆,伯恩著,邹智敏译:《社会心理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同时,在我国学者周晓虹主编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探索》一书中,歧视被认定为“针对特定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不公正、否定性的行为”周晓虹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探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0页。。持此相似观点的还有俞国良,他将歧视界定为“直接指向偏见目标或受害者的那些否定性的消极行为表现。”俞国良:《社会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二是以社会学为界定视域,主要代表为波普诺。他强调,作为一种行为的歧视,更准确地说,“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之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美)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不难发现,在这两种视域之中,对歧视概念的界定存在着这样的几个共识性规定:其一,歧视的本质是一种具体行为,而非抽象意识。其二,不公正/不平等是歧视的根本价值质性,并以此标识出歧视的实践性质,规定着歧视的实践影响。其三,歧视具有一定的对象,能承接主体发出的歧视性行为,从而形成完整的映射弧。
此外,从法律视角对歧视进行发思也是当下定义歧视的重要方式。相同的是,在这一视域之中,对歧视的认识也具有上述几个共识性的识见。但不同的是,以法律视角来定义歧视往往涉及到对歧视的判断,认为歧视具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和“尊严是判断歧视的重要要件,”李薇薇:《反歧视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关系到对作为对象性存在的人之基本权利的不尊重或侵犯。这种不尊重或侵犯或是因主观恶意造成的(直接性),或是作为无歧视性意涵行为之结果(间接性)。这即意味着歧视的存在样态不仅表现为一种具有直接性的具体行为,也体现为在行为结果上表现出对行为对象之基本人权的不尊重或侵犯,尽管造成这一结果的行为本身不具有歧视性意涵。由此,我们可以尝试为慈善歧视做一个可能释义:即慈善歧视指的是在慈善活动中出现的对慈善对象不公正、不平等的慈善行为,或在无不公正、不平等慈善行为中出现的背离公正、平等,形成对慈善对象基本人权的侵犯或不尊重的慈善结果。
然而,对于慈善歧视这一可能释义,仍存在着进一步澄清与辨析的需要,以使其内涵和外延更精准化和规范化。
首先,需要深入辨析的是作为慈善歧视概念释义构成要件的“慈善对象”。
所谓对象,从哲学语义而言,对它的认识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即论及对象,则必然包含着与之彼此依存、具有意涵性关联的主体,并认为对象与主体意义上的自我一同构成获识感性确定性的基本条件。同时,在逻辑哲学看来,对象是知识产生的基础,无对象即无知识 。此外,对象也是普遍的、客观的、相对的存在,任何人、事、物都可以成为对象性存在,任何活动都是对象化实践。对象的存在为深度考察人、事、物提供了可能通道。正如维特根施坦所指认出的,“给出了所有对象,由此也就给出了所有可能的基本事态。”(奥)维特根斯坦著,韩林合译:《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页。
故此,考察慈善对象,必将涉及慈善主体。从供需角度来看,慈善对象是慈善需求者,慈善主体是慈善供给者。两者发生直接慈善关系是慈善活动的传统图景,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慈善互动模式,即慈善供给者直接援助慈善对象。并且,结成这一直接慈善关系的双方呈现出由熟人走向陌生人的发展趋势。诚如上文所论及的,任何人、事、物都具有成为对象性存在的可能与属性。但在社会慈善的传统图景之中,因慈善需求者与慈善供给者发生的是直接慈善关系,且受“施在上位,受在下位”的传统慈善理念影响,慈善主体通常不构成被挑选的对象,也就意味着两者在身份上具有唯一性。因而可以说,在传统意义上,构成释义慈善歧视概念要件的慈善对象在指向上有且仅有慈善需要者。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慈善发展的自我需要,传统慈善在实践方式上已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并发展出适合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实践图式。这集中体现为:慈善供给者依托慈善组织为慈善需求者提供慈善援助。进而,这即意味着慈善供给者与慈善需求者发生的是间接慈善关系,而非直接慈善关系。这是一种复杂化的慈善互动。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更是深刻变革着传统慈善的理念及方式。陌生人之间的慈善互动也成为慈善常态。其中,不言自明的是,慈善需求者仍旧是慈善对象的基本构成。但此时的慈善供给者以及充当“中间人”的慈善组织是否能成为慈善对象?这需要从现代慈善的运作方式加以检视。当慈善供给者凭借慈善组织与慈善需求者发生关系时,慈善供给者存在着或因自身具有的认知偏见、或因错误信息的干扰等,对慈善组织进行显失公正的排序和选择的可能,从而导致慈善组织被不公正对待。与之同时,设立慈善准入门槛,如规定慈善捐款最低额度,也常见于现代慈善之中。无论其本质如何,在形式上都表现为对慈善供给者进行序位等分,并造成对处于门槛红线之下的慈善供给者的排挤,形成对慈善供给者的不公正对待,剥夺慈善供给者的慈善资格。由此不难发现,在现代慈善中,被歧视的慈善对象不仅有慈善需求者,也包括慈善供给者和慈善组织。
其次,有待深刻澄清的是慈善歧视与慈善差异的关系。对两者关系的辨证,一方面能避免对两者的混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慈善歧视的外延。因为两者之间既存在交集,又不完全等同。在大量情形中,人们将不平等/不公正待遇视为差异对待,这就导致形成了混用歧视与差异的惯性结构。但必须追问的是,差异对待就等同于歧视吗?所谓差异,指的是“事物及其事物的运动过程的不同或差别,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相对性等特征。”邱耕田:《差异性原理与科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8页。
差异存在是人、事、物的最大现实,也是其得以区分的本质标识和形成独特性的本源所在。与差异相伴存在的即是同一。同一是对根本质性的认识,并以此确定类属,是平等的来源与根据。诚如《人权宣言》所强调的人生而平等的价值理念,就在于同为人这一类的存在。差异与同一辩证互动,只有在同一中才能更好地诠释差异。从上述意义而言,差异对待即存在着两重具体意涵:一是因事物及其运动过程具有的非同性,而采用的与事物独特性相匹合、相适宜的差别化对待方式。二是对平等的背离,以差别化的多重标准对待同类存在,内含公正理念的丢失。相应的,慈善差异即存在着如此这般的两种释读和具体化的实践行为。其中,前一种情形的慈善差异非但不属于慈善歧视的内容所指,相反,它却是促进社会正义的慈善力量。如针对两性独有的重大疾病的慈善援助,更利于两性和谐。而后一种情形的慈善差异则表征的是慈善歧视。
二 慈善歧视的集中表现
慈善歧视既然作为一种行为或结果,就存在着具体的表现形态。总的来看,慈善歧视集中表现为目的性歧视、规则性歧视和选择性歧视。
(一)目的性歧視。这指的是在设立具体慈善目的时发生的歧视。目的是行动的导向,也是行动的实践指向。发生在慈善目的中的歧视具有两重表现形态:其一,慈善目的携带着强烈的功利性意涵。具体来看,“利他”是社会慈善的原始目的。伴随着人对自我、自然以及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一元化的利他性慈善目的逐渐走向二元化,即“利他”与“为我们”并存。因为人逐渐认识到必须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保障人之存续。如对保护水资源、环境、卫生、空气等慈善涉及,是对我们公共福祉的促进。但与此同时,一个发生了性质嬗变的慈善目的即“利己”也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从而为慈善目的增添了功利性色彩。表现在现实之中,即是将慈善异化为“利己”的工具,并诉求于自我价值的最大化。诚然,这种利我的功利性慈善目的本身可能不携带歧视性意涵,之所以将其视为目的性歧视的一种表现,主要在于行善的功利性追求可能体现出对社会公平公正的破坏。2010年重庆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为鼓励慈善,联系市教委直属中小学订立了以重点学校就读机会回报慈善捐赠的“道德协议”2010年1月6日,重庆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为鼓励爱心人士积极募捐,联系市教委直属中小学对捐赠者给予回报:捐赠500万元以上的个人,其子女或直系亲属可免费就读市直属重点中小学;捐赠500万元以上的单位,职工子女可优先入读市直属重点中小学。此则消息一出就引来了学者、媒体、社会大众的广泛批判,一个核心认识即在于,认为这是以慈善践踏了社会公平公正。,就使功利性慈善目的中充斥着破坏社会公正的实践意指。同时,受这一目的驱动,也可能导致在具体实践中造成对慈善对象的不公正对待。
其二,慈善目的自身携带着歧视性意涵,无关功利性追求。这是目的性歧视的主要体现,通常表现在慈善目的中设置多重非公正的限定性条件,从而将一定对象驱逐于慈善之外,使其不能获得慈善援助。这一携带着歧视性意涵的慈善目的在本质上是对人之平等的价值理念的背离,并造成人在进入慈善之前就受到不公正对待。一个经典的目的性歧视案例就是马修·哈丁所论及的“以向‘白人基督教新教男性提供大学奖学金为目的的信托。”(澳)马修·哈丁著,吕鑫,李德健译:《慈善法与自由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87页。这内在地以人种、宗教信仰、性别等多重规定将本应人人具有平等获得奖学金的慈善资格,转变成了特定人的特定福利。同时,2008年,《我们为什么不愿领养残疾孤儿》2008年,我国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导致众多儿童成为孤儿,其中不少儿童在地震受到重创,留下残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领养这些儿童的热潮。艾冰女士所在的报社组织了认养灾区孤儿的活动。她就爱心人士认领灾区孤儿的“要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那些在灾难中留下残疾的儿童往往不构成爱心人士的选择对象。艾冰:《我们为什么不愿领养残疾孤儿》,《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19日,第002版。一文引起了社会对慈善的广泛讨论。文章作者通过总结和分析众多爱心人士认领灾区孤儿的所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即我们的爱心人士并没有一种对灾区孤儿的“特殊眷顾”,他们在认领灾区孤儿时,所彰显出的爱仍然没有超越“自我需求”的狭隘慈善理念,因为那些在地震中致残的孤儿往往被排斥在他们的认领活动之外。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些爱心人士所提出的“认领要求”作为慈善的“目的性条件”,如“最好没有残疾的孩子”这一“认领要求”,所表达就是“我的目的是认领一个健全的孩子”。如此,不难发现,这一慈善目的内在地就存在着排斥残疾儿童的实践预设,体现出一种不彻底,有“私心”的爱。
(二)规则性歧视。这指的是进行慈善的规则具有歧视性意涵。它既涉及到慈善规则制定的非公正性,也关系到慈善规则适用的非公正性。前者集中体现为设立个体或团体的慈善准入规则,即设立最低捐赠额度和慈善时长。在一定程度上,这具有积极意义,能增强慈善援助的效用性和延续性。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则的设立往往产生背反效果。它将人人自愿可为的慈善变成了只有部分人能进行的道德实践。这在形式上就表现为,要想进行慈善的个体或团体只有具备购买捐赠物资和时间最低限度的能力,才能进行慈善。而能力相对未能达到最低限度要求的个体或团体则被排除在慈善之外。从本质而言,这是以资格基础偷换慈善的人格基础。一个重要的现实表现就是我们的“行善标准起点高。”王振耀:《如何突破行善理念的封锁线》,《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第25页。根据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2018年版)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见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2018年版)第二章第八条。这在客观上阻碍了部分人希望行善的道德愿望。早在2012年,《重庆时报》就曾刊发关于为爱心设立捐款门槛的批判性评论。这认为慈善评奖中设立的捐赠资金要求,会给公众传递出“捐的越多,就爱心越大”的错误慈善理念,强调对慈善爱心不能以金钱为以衡量。参见(曹林)《为爱心设捐款门槛令公众寒心》,《重庆时报》2012年1月4日。尽管它所强调的是慈善不应该以金钱作为衡量其大小的标准,但也从侧面上反映着在社会中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慈善景象,即为慈善捐赠设立门槛限制,从而导致慈善的人格基础被消解。
而后者则在慈善活动之中层见叠出。从慈善的行为主体来看,这表现为相较于慈善对象,慈善规则对其的约束力具有失衡性。因受“施”在上位和“受”在下位的传统慈善观念影响,周中之:《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伦理追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6期,第83页。加之慈善行为主体具有的相对优势地位,易使其形成对象性优越感,从而在践行慈善之中易发生伤害慈善对象尊严的暴力慈善,且无明确的对这一暴力慈善进行规治的规则安排。诚如发生在公益助学行动之中的,要求被资助的学生撰写并当众朗读感谢信,以及在大众面前举着资助金额的支票拍照等众多伤害其尊严的“慈善景观”。而从慈善对象来看,其与慈善行为主体的熟悉度、亲密度等,能对慈善行为主体如何抉择产生极大影响,进而易导致具有“亲亲相隐”性质的慈善出现。一个常见的表现即是,相较于陌生人,我们更愿意援助熟人。此外,慈善规则适用的不公正还表现在,以“一刀切”的硬性做法对待所有慈善组织。我们知道,慈善组织具有规模之分,以规模的大小可以将慈善组织分为大型和中小型。两种类型的慈善组织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和发展压力。诚如加里·莱西(Gary Lacey)等人所指出的,在中小型慈善組织中强行使其遵守与其他慈善组织一样的道德规范是对它生存现状的不公正对待。Gary Lacey,Betty Weiler ,Victoria Peel.Philanthropic tourism and ethics i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a case study in Central Kenya.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16,Vol.41,No.1,pp.16-25.因为它所面临的生存压力较其他慈善组织大得多,因而难以保持住与其他慈善组织同一层级的道德规范。
(三)选择性歧视。这指的是在具体进行社会慈善的过程中,发生在慈善选择中的歧视,常表现对具有不同性别、身份之人的不公正对待。更为详细地看,对具有不同身份之人的慈善不公正对待,一方面体现为因某人具有某种身份而将其拒斥在慈善之外,拒绝为其提供慈善援助。诚如上文提及的拒绝为服刑结束后的人、同性恋者、陌生人、不同肤色者等提供必要的慈善援助。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因慈善组织具有某种身份而发生的对它的不公正对待。这主要表现为,我们以规模的大小对慈善组织进行的区分,在一定意义上也赋予了慈善组织某种身份认定,进而在慈善资源的社会来源上就极易出现不公正倾向的风险,即我们形成了将物资、时间、服务等捐赠给大型慈善组织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从而易导致中小型慈善组织产生被不公正对待的体验。此外,因身份造成的慈善不公正对待还体现在因个体身份差异而受到慈善资源的非公正性分配。比如开篇论及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市红十字对社会捐赠的防疫物资以非公正的方式分配给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
而对不同性别的不公正对待,则存在着三种基本情况:
一是发生在现实之中的因性别差异而将其排斥在慈善之外,体现出绝对的排他性。在慈善中就体现为单一性别偏执,如只援助男孩,尽管女孩更可能需要慈善援助。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发起的“代理爸妈助养一对一”慈善项目,在实施之初,其“性别选择”一栏只有“男性”,而无“女性”。尽管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是系统问题和可能是女孩已经都获捐助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发起的“代理爸妈助养一对一”慈善项目,在实施之初无法选择儿童性别(只限定为男)。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大众关于慈善之中性别排斥的讨论。参见(应悦)《孤儿资助慈善项目只能选男?回应称可能女童都已获捐助》,《新京报》2019年12月18日。,但仍旧引起了关于慈善援助中性别排斥问题的广泛讨论。在一定意义上,该项目在系统设置上犯的错误所体现的即是传统的两性不平等观念在慈善实践之中的现实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具有绝对排他性的慈善实践意识与“定性化”的慈善援助存在着本质区别。在现实中,我们可能经常看到女性慈善援助计划(只面向女性),如针对女性生育健康、教育保障等的慈善援助。这种“定性化”的慈善援助不是对男性的不公正,而是源于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做出的促进两性正义的慈善实践。但也需要看到的是,即使在这种“定性化”的慈善活动之中,也存在着“性别渗透”现象,比如在以救助失学女童为核心的“春蕾计划”1989年人口普查之时,发现我国有超过400万适龄儿童无法上学,其中,80%以上的都是女孩,由此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实施的儿童公益项目,用以资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继续学业的“春蕾计划”诞生。2019年12月,春蕾计划被爆出在“一帮一助学”活动之中,受助对象为男生。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随之回应因有教师反映男生也需救助,故此1267名受助的高中生中有453名男生。这一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对春蕾计划“诈捐”的责难,也有人指出这是性别歧视的重要表现。之中,就曾出现男性占比不小的现象,侵害着女性的慈善权益。
二也是发生在现实之中的因性别差异而存在的不公正慈善对待。相较于前者,这体现出的是相对的排他性。一方面,从女性作为慈善的行动主体来看,这表现为在从事慈善工作之中不给予她平等的慈善待遇。《南方周末》文中对男女两性在从事慈善工作时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开展批判,认为这是性别不平等在慈善事业中的體现。参见(汪徐,秋林)《女性做公益,就该低收入吗?不平等与偏见》,《南方周末》2018年9月13日。就曾报道有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女性在我国公益从业者中占比过大半,但其薪资整体水平较男性偏低。这所反映的是社会普遍存在着的两性“同工不同酬”现象在慈善事业之中的延伸,根本指认着在慈善行业中存在着性别不公正的实践气质。尽管女性慈善行为自古有之,并在慈善事业良性运行、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推进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周秋光,贺蕃蕃:《中国女性慈善实践的历史与现状思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55页。“能让慈善更具力量。”2016年3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妇女慈善研究中心主任黛博拉·梅斯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举办的“女性引领慈善”公开课上,就记者关于女性做慈善有哪些优势的提问,回答到“女性可以让慈善更有力量。”另一方面,从女性作为慈善对象来看,这则表现为对其的慈善关注力度、深度等不及男性。姚明爱心基金会姚明爱心基金会主要关注乡村体育教育,组织学生篮球队。该项目打破了“篮球是男生专属运动”的刻板印象,要求女生球员比例不能低于20%,并制定了激励女生参与的规定。这是性别平等理念在慈善实践之中的重要体现。刘天红:《慈善事业中纳入性别视角的挑战和策略——关注“2017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中国妇女报》2017年7月4日,第B2版。可以说是与之相关的正向体现。由它资助的“春渠”篮球队中,有不少女性球员的身影,并制定了激励女生参与的赛制规定,体现着性别平等的慈善理念。同时,也隐喻着在慈善活动之中可能存在着的两性关注力度不公正的实践现象。
三则是存在于慈善观念之中的携带着偏见性意味的传统性别意识。根据《中国发展简报》发布的一项以“公益行业中社会性别现状和挑战”为题的调研报告,不少慈善组织就招聘、出差等众多方面在观念上仍停留于传统的性别意识上,认为女性需要照顾家庭,体力不如男性等,而不将其作为出差的意向性对象。根据2015年《中国发展简报》发布的以“公益行业中社会性别现状和挑战“为题的调研报告,在安排出差活动(含培训、参会、开展项目等)时,有33家机构“不考虑性别因素,根据员工能力和意愿而定”,但这33家机构中有2家认为“该出差需要体力、或可能有危险,因此优先考虑男性”;2家认为“男性更适合应酬、交际,因此相关出差优先考虑男性”;还有1家认为“女性要照顾家庭,因此更倾向于安排男性出差”。这在根本上所传递出的是根植于文化心理的传统性别偏见,从而导致女性在现实的慈善活动之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深度发思“公益慈善与社会性别”也成为了近年来重要的慈善议题。如由联合国妇女署在北京主办的“2017社会性别与慈善发展国际论坛”、我国在成都举办的“2015西部公益论坛”等都将“公益慈善与社会性别”作为重要议题加以研讨。
三 慈善歧视的主要成因
慈善歧视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见表1)。从客观上而言,慈善发生所需的必要条件和慈善资源的有限性提供了慈善歧视的孵化可能。
先看慈善发生所需的客观条件。这里所论述的客观条件是慈善之能发生和存在的根本可能。即慈善存在于差异,无差异则无慈善。王银春:《社会慈善:基于差异与否定差异》,《伦理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4页。诚如上文所论及的差异存在是人之最大现实。这种差异化的存在不仅造成每个人具有不同的生存机会,也恰恰是慈善发生的必要条件。因为慈善作为向一定个体或群体捐赠物资、时间和提供服务的实践,就意味着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一定存在着财产上和能力上的差异。假若个体之间或群体在财产和能力上具有同质性,就不需要发生慈善援助。王银春:《社会慈善:基于差异与否定差异》,《伦理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5页。但也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慈善歧视才有了客观的产生可能。这具体表现为:差异为形成偏见性认识提供了滋生土壤。
详言之,歧视来源于偏见或是偏见的现实化表现,已在多学科上得到普遍承认。偏见的本质是一种“针对特定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不公正的、否定的态度”周晓虹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探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0页。,持有偏见的人在面对或想到这一对象就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而偏见的产生不仅具有鲜明的个体根源,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周晓虹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探索》,第263—264页。——人的差异化社会存在。特别表现为因人之社会地位、权力以及财富占有等的差异,而形成对特定群体及其成员充斥着偏见性认识的刻板印象,并在其驱动下实施不公正行为。一个经典样本就是西方国家泛化存在的阶层偏见,并以穷人区与富人区的地理坐标加以区分,凸显阶层优越感。延伸到慈善之中,也就意味着差异在为慈善发生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也制造着慈善歧视出现的机会。
再看慈善资源的有限性。有限性是考察人及其生活世界的重要通道,也是确立出人是现实的、此在的存在的重要根据。这在于现实之中的人及其生活总是受到特定的时空以及生产方式等的限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有限性和人的有限性的存在方式这一基本现实陆杰荣,牛小侠:《“历史”范式的演进与人类“有限性”的研究》,《求是学刊》2012年第4期,第26页。。尽管基督教神学对人的自由发展造成了极大压迫与荼毒,但它将有限性视为人之生存特征,仍是对人之存在的积极探索。质言之,“有限性不仅是人的外在基本特征,而且也是人的内在基本结构。”陆杰荣,牛小侠:《“历史”范式的演进与人类“有限性”的研究》,《求是学刊》2012年第4期,第28页。因此,不言自明的即是,慈善作为人之生活实践,也就存在着资源有限的客观事实。而这,即为慈善歧视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慈善资源的有限性带来的慈善歧视的发生可能,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有限的慈善资源在数量上与慈善需要存在着不对等关系,即慈善需求者数量胜于可供使用的慈善资源。二是多样化的慈善需要与有限的慈善资源相紧张,即慈善资源在内容上难以实现对多层次慈善需要的并济。从而在分配慈善资源的各环节上,就极易发生不公正,形成慈善歧视。
而从主观上来看,慈善歧视的产生与慈善行为主体的动机和选择紧密关联。在一般意义上,如何选择受动机驱动。以慈善动机的不同性质区分慈善类型已成为普遍识见。当下,依据慈善动机,慈善被分为含一定功利性的慈善与非功利性的慈善。周中之:《慈善:功利性與非功利性的追问》,《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3页。在这两类不同质性的慈善之中,都可能发生慈善歧视,但其发生的可能不仅具有相同性,还存在独特性。
就相同性而言,发生在两种类型慈善之中的歧视都可能源于偏见。这在于偏见不仅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更具有在个体生命历程的各个时期都发生的可能。偏见作为人之态度的一种,往往使人在消极的情绪之下做出未经理性审思的行为。所以偏见携带着感性的色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页。且人对社会关系的建构贯彻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这即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是不断生成的,因而人也是处于不断生成之中。所谓生成也就是人在智识、道德、能力等方面的不断“进化”,并不断褪去感性的支配、获得理性抉择能力的过程。由此可以说,人并非生而就智识完满、德性完美、能力完全,而是时刻处于理性与感性的博弈之中。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之认识的经典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即包含着人是时时在追寻理性和向理性靠近的意涵指向。因而,对偏见的修正也只有进行时,贯彻于人之生命历程。这表现在两种类型的慈善之中,即是行为主体都可能因理性认知的不足和非道德圣贤的制约而在进行慈善时作出不公正的行为。
从独特性来看,发生在功利性慈善之中的歧视,主要受功利性目标的诱发。这是“投资—回报”模型在慈善之中的重要体现,即慈善行为主体在实践立场上将慈善视为一种投资,其所考量的是进行慈善能为自身带来多大的回报,如经济收益、形象构建、社会地位等,并偏执于追求更高回报,从而将自身具有的慈善资源集中于能为自我带来更大价值的慈善对象上。因而在进行慈善选择时,其遵循的不是社会正义原则,关切的核心不在于推动社会和环境发展,而是个体效益原则,从而会造成对未能给自身带来高回报的慈善对象的不公正。萨拉蒙就曾对慈善之中的这种投资回报理念展开深刻批判,认为它消解了“影响力投资”在慈善之中的原初道德意义。(美)莱斯特·M·萨拉蒙著:《撬动公益:慈善和社会投资新前沿导论》,叶托,张远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而发生在非功利性慈善之中的歧视,则主要存在着三重诱发因素。其一,慈善行为主体从自然之中形成的无意识的选择习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是人在进化发展中体悟到的自然规则。从这种自然规则之中,人形成了“求强”的选择意识,并在长期发展中沉淀为人的心理结构,促成了这种选择意识向本能性选择即无意识性选择的转化。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扶强不扶弱这一具有自然式选择特征的选择习性。从而在非功利性慈善之中,当面临选择,因受这种由自然之中形成的无意识的选择习性的影响,偏好较强者成为选择常态,进而导致对被认定为较弱者的不公正对待。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公益助学中,选择优等生的比率远胜于非优等生,尽管非优等生慈善援助的需要可能更大。
其二,共情程度。共情,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社会化方式,即情感的共通。这能对如何选择产生极大影响。共情的重要体现就是同情心。而这一认识——同情心是慈善发生的内驱要件——在历史上已完整建立,如休谟等人就将同情心视为促进慈善发生的重要动力条件。由此可以说,慈善发生的内驱力是慈善行为主体对慈善对象产生了共情体验。但需要看到的是,不同情感之间却存在着引起共情体验的价值序差。亚当·斯密就曾深刻地指出,“我们对悲伤的同情,就某一意义来说,比我们对喜悦的同情更为全面与包容。”(英)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同时,在同一种感情中,共情的发生及其程度也存在着差序形态。如对苦难形成的感同身受越强,进行苦难援助的可能就大。因此,慈善行为主体与慈善对象产生的共情越强,就越可能进行慈善援助。这也就意味着能使慈善行为主体产生更强共情体验的慈善对象,就越能成为被选择的对象。从本质而言,这是基于情感的感性思考,具有直接性,仅从情感上决定着慈善选择,难免会发生不以同一标准为抉择尺度,从而造成在选择过程中出现不公正现象,特别是当情感偏执这一情况发生之时。
其三,发展性考量。这指的是慈善行为主体以慈善对象的可能发展为其做出抉择的依据。具体表现为慈善行为主體积极关注慈善对象的可能发展,并将慈善资源偏向于具有更大发展可能的慈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性考量与慈善行为主体无意识的选择结构,在具体表现具有相似性,即都偏向更优的慈善对象。但两者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发展性考量是一种有意识的积极行为,内含着一定的理性思考;而慈善行为主体因无意识的选择惯性所做出的慈善抉择,则是未经理性审思的消极行为。尽管慈善行为主体在本意上可能没有歧视的意涵,但对那些被判定为发展可能性相对较低的慈善对象而言,受到不公正对待是既定事实,易导致其产生被歧视的情绪体验。
四 慈善歧视的消极影响
慈善歧视具有多重消极影响,不仅破坏慈善的功能结构,也偷换现代慈善的价值原则,更有可能诱发新的社会风险。
首先,慈善歧视背离促进分配正义的慈善功能。从分配方式而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社会分配的两种基本方式。初次分配遵循贡献原则,以贡献量确定分配值。“按贡献分配本质上是按差异原则分配,”易小明:《论差异性正义与同一性正义》,《哲学研究》2006年第8期,第116页。是对人之差异存在的确认,体现差异正义的价值意涵。再分配是建立在初次分配之上的,通过税收、社会福利、转移支出等方式对社会差异的调节,旨在弥合社会差异,促进整体共同发展,是对人之同一性的肯定。社会分配的这两种基本方式都是分配正义的体现。不难发现,慈善并不属于社会分配的基本方式之一,那么慈善如何具有促进分配正义的功能?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看来,慈善是实现正义的重要路径,它涉及到包含着分配在内的多种正义的实现。但洛克、斯密、康德等人对慈善促进分配正义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相较于慈善,分配正义的实现更有赖于制度性的社会保障(国家强力)。这是对慈善具有促进分配正义功能的不彻底性否定。相较于这种不彻底性否定,罗尔斯与斯威夫特则认为慈善与正义无关,进而慈善不存在着对分配正义的促进功能。但需要看到的是,正义作为抽象概念历来被适用于不同行为、关系之中而具有诸多表现形态和价值意指,如交换正义、性别正义、规则正义等。这就意味着建立在罗尔斯与斯威夫特“慈善与正义无关”根基上的“慈善与分配正义无关”的线性认识具有内在的逻辑弊病,即两者不是简单等同关系。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罗尔斯与斯威夫特所强调的慈善与正义无关指的是慈善与交换正义和矫正正义无关。吕鑫:《当代中国慈善法制研究:困境与反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40—151页。在当下语境之中,我们更多地秉持着慈善能够促进分配正义的价值识见。这首先在于,慈善能通过捐赠物资的方式,促进物资向弱势群体的流通,从而实现物资的再分配,做到分配正义。其次,“当代的慈善活动本身已经被纳入国家的税收调整之中,”吕鑫,王凌皞:《论慈善与正义》,《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第257页。这就直接参与了再分配,与分配正义发生关联。但与再分配不同的是,慈善依托个体或团体的自觉自愿,具有“软性”特征;而再分配则以社会规则为支撑,具有“硬性”特征。慈善也因此被称为第三种分配方式。
但慈善歧视却是对慈善促进分配正义功能的背离。这具体表现为:一是作为慈善行为主体的“我”与作为慈善对象的“他”之间的社会差异进一步扩大化。如发生在以“利己”为目的的功利性慈善中的歧视,以“我”的收益为核心追求,慈善被异化为撬动“我”之物资增值的杠杆。且在通常情况下,物资的增值额远大于投入额。就像伊恩等人(Iain Hay)所看到的,慈善家的“慷慨”实际上是在“资助他们自己”而已。Iain Hay and Samantha Muller.Questioning generosity in the golden age of philanthropy:
Towards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super-philanthropy,Prog Hum Geogr,2013.因而,这尽管在形式上保留着慈善的面相,但实质上已造成慈善失真,不仅未能促进人之社会差异的弥合,相反,却进一步拉大了人的社会差异。此种情况下,慈善关注的不是分配,而是再生产。二是作为慈善对象的“他”受到分配的非公正对待,导致分配的正义内涵丧失。慈善资源在慈善对象上的不公正分配是慈善歧视重要的现实表现。特别是因偏见性认识等因素而将一定的对象排除在慈善之外,导致其不能参与到慈善分配之中,相悖于慈善的分配正义理念。
其次,慈善歧视以“条件准入”理念置换人人具有慈善共建权、共享权的价值原则。慈善作为人之古老传统和实践活动,在现代转型中实现了道德祛魅,即“慈善行为挣脱了纯粹‘利他主义动机的道德枷锁,被‘还原为一个现代公民履行的社会责任,成为日常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刘威:《解开中国慈善的道德枷锁——从“恻隐之心”到“公共责任”的价值跃迁》,《中州学刊》2013年第10期,第67页。与责任相对存在就是权利。这意味着当我们对慈善进行道德祛魅时,就存在着赋予慈善以权利为存在样态的实践指向。在现实生活,人对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慈善援助的积极主张,也暗含着慈善是人的一项权利的价值意蕴。诚然,权利的存在需在法律中确立。早在17世纪初,英国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后又经多次修改。而后,慈善法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在慈善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反思新问题、吸纳新经验,推陈出新。2016年我国颁布首部慈善法,慈善活动由此正式进入法制轨道。因此可以说,对慈善在权利意义上的承认有着历史悠久的法律确认。从参与方式来看,慈善作为一种权利可分为慈善共建权和慈善共享权,即人人都具有进行社会慈善和享受慈善援助的平等资格。这源于慈善自出现伊始就具有的人之平等的高位格价值理念。但无论是慈善歧视的何种表现形态,在本质上都体现的是“条件准入”的慈善实践图式,即符合条件则进入,不符合则排除在外。我们承认在一般意义上,条件的设立有利于选择更适合的对象。但前提是这一条件的设立应满足公正、平等的资格审查。而慈善歧视中所内蕴的“条件准入”模式却充斥着浓郁的非平等色彩,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从而导致人人具有的慈善共享权和共建权被以“条件准入”的方式偷换为部分人的权利。这不仅导致慈善高位格品质的丢失,也背离了法律保障公正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