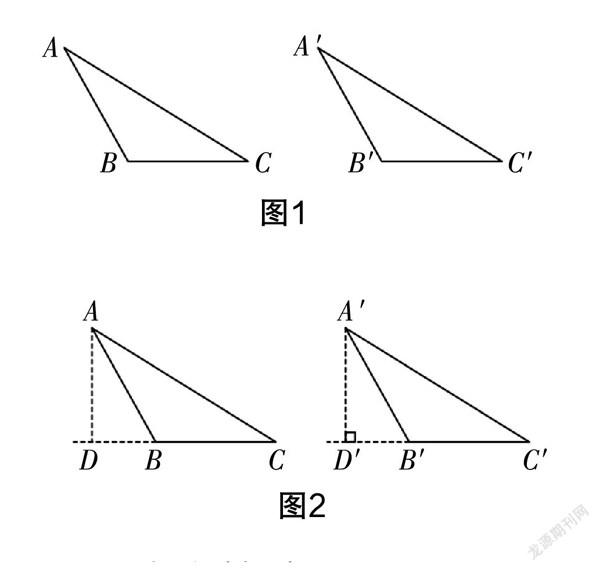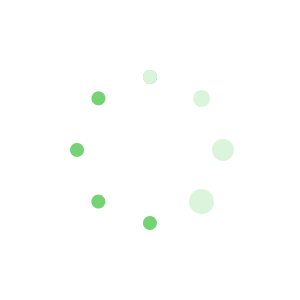编者按:2020年4月1日,收到《内蒙古教育》雜志社孙志毅主编的微信,他告诉我,他今年元旦后退休了。他说以后在全国的总编、社长会议上见不到大家了,他嘱咐我“天涯若比邻,以后不要断了联系啊”。随即,他发来自己的《我的阅读史》,阅读,这正是我至今十分在意的一个话题,看来也是他心念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是2018年8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全国教育报刊社社长、主编会议上认识孙主编的。之后,加了微信,常去他的朋友圈学习,不断有交流。“从一个人的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味”。的确,朋友圈的孙总是有趣的,比如一盘自己种的蒜苗,他会拍个照,发几句感概“我种的蒜苗,多像今日社会的知识分子:有勇敢昂起头颅的,有低下脖颈装睡的,有的压根儿就把自己龟缩在蒜皮里,偷生……”;比如从填写一份“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他会抑喻道“我有煤矿吗?我有煤矿的股份吗?感觉没有,但细想又有——国有煤矿是国家的,国家又是人民的,我又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因而,我是‘有煤矿的人,哪怕是煤矿的一个螺丝钉,一片煤矸石……”;他看《美国简史》、《心血运动论》等书,然后对比,发现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可不始于明代,而是始于公元前;他的朋友圈还有“原生态的妈”,有“儿子领着自由行”的亲情;更多的则是他的教育随笔,针对教育教学,针对教育案例,一事一议,很见功力,回味隽永。
他的这篇阅读史,以时间为经,将各个阶段的阅读故事串联起来,从中我读到时代的变迁和渴望精神成长,一代代中国人艰难困厄的心灵历程,启示在阅读学习的时代大潮中,怎样让阅读更好地助力我们的精神成长,以反拨难以提振的全民阅读率。
真真切切地记得,我的“阅读元年”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的。五十多年了,如在昨日。
那天,随四合院的李家老二,到他的三姨家串门。三姨家住在县城衙门口的一处小院,旁边就是县图书馆,邻家三姨和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是闺蜜,三姨可以随便借出馆里的图书。
那天,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在三姨家看到一本长篇小说《平原枪声》,入神地趴在炕沿上看着。三姨那时候也就三十多岁,好奇地问:你这么小,字认不了几个,能看懂吗?
那时的我,确实拦路虎一堆,还分不清“士兵”和“土兵”。只羞涩地答道:我能看懂一半。
这大约便是我的阅读元年。
那时,我所就读的小学叫“顺城街小学”,全校由四个民国时期的商号小院串联而成。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管理图书的是美术老师毕海,但三年级以下学生不借,好不容易熬到四年级,每周五的下午最后一节课便可以去借书了。下课的钟声一响,几个爱上阅读的同学就箭一般地冲出教室,你推我搡在图书室排起了长队——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屋子,也没有多少藏书(有没有自己今天的藏书多都值得怀疑)。因而去晚了就借不到了。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6年。
那时,在学校借到的书至今还能记住书名的有《十五贯》《金枝玉叶》《红旗谱》《十万个为什么》等,逮着什么看什么,有字就成。饥饿的孩子啊,吃什么都香。
后来学校及县图书馆被封存了,但人们阅读的欲望是无法封存的,阅读转入地下——我家的四部藏书保存下来了。这四部书分别是:吴晗写的古代著名战役的通俗读物《古战场》,至今还记得,里面有春秋时期的齐赵“长勺之战”及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第二本是《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7卷,说的全是内蒙古西部地区辛亥革命时的历史;第三本是《彭公案》,清末的那类长篇公案小说,还是线装的。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被鲁迅评判为“亦不外贤臣微行,豪杰盗宝之类,而字句拙劣,几不成文”。此外,还有一本前后受损严重的《尺牍》,是古人写信用的工具书,父亲一辈子写信以它为标准,无一次行款出其格。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给我写信,开头仍然是“吾儿志毅,见字如晤”之类。
欧阳山的《三家巷》、巴金的《家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陈立德的《前驱》、杨益言和罗广炳的《红岩》等,就是我在1966年到1972年间阅读的。
1970年前后,隔壁发小韩亮家突然有了许多书,全是精装本的外国名著,土黄色的封面上印着黑色的书名。现在能记住书名的还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论法的精神》,有莎士比亚戏剧集中《第十二夜》等等。原来是他的姐夫所在的兵工厂将由包头迁往山西宁武,因携带不便,暂时存放于他们家。
在今天人看来感觉奇怪和惊讶的是,一个工厂的钳工,充其量是个技术员,怎么会购买、收藏、阅读如此高深的西方名著?可惜那位只见过一面的姐夫四十多岁就被胃癌夺取生命,我无从知道他的阅读史。但这位姐夫留下的那些硬梆梆的西方名著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的精装的、西洋的名著。
十五六岁的我们饥不择食,凡是有字的,一律读,囫囵吞枣、半生不熟,都是无所谓的。有点像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那个被囚禁的科学家一样,便是棋谱,也得掘地三尺、如饥似渴地读。
后来,四合院搬来了一对新婚夫妇,新娘子的母亲是我母亲的故交,所以我们叫她“莲梅姐姐”。
“莲梅姐姐”算是“老三届”那一茬儿,二十出头的样子。隔几天她家就出现一些苏俄小说,不知道从哪里借到的,如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没办法,谁让自己想看呢,就腆着脸说:“莲梅姐姐,你借给我《罗亭》看,我就给你担一个礼拜的水,行不?”
莲梅姐姐犹豫了半晌,居然答应了。
以劳动换来一本书读,是那时少年的我最大的幸福!
1974年4月10日,18岁的我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下乡插队,到一个离丰镇城东40多里、晋蒙接壤的乡村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的农业基本还处于汉朝“二牛拉犁”时代,全大队只有两台耕地的拖拉机,全村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但农民很看重自己的专业化:“三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会一个庄稼人。”算是唯一的一个自信!
一卷行李、一个脸盆、一把锄头,走了。母亲边拉着风箱,一边抹着眼泪,默默地给我做了最后一顿饭……
公家免费送了一纸箱书:《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哥达纲领批判》《波拿巴雾月十八政变》《哲学笔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无书籍可阅读,无未来可憧憬,无远方可梦想的日子里,这些马列经典就是我唯一的藏书!
就那时我的文化积累而言,说自己读懂了什么,连鬼也不信!每一部书都涉及纠葛纷繁的欧洲历史,诘屈聱牙的外国人名,欧化的译文,高深莫测的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原理。最好懂的算是《国家与革命》和《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和《共产党宜言》。
下乡插队的五年里,看得最多的是“两报一刊”,梁效、罗斯鼎(实为写作组)之流的批判文章每篇都看。每个礼拜,保管员老史腋下夹着一卷报纸一晃一晃地从大队回村时,一定经过村西那一排知青的房子,我们便拦住他,把报纸要了下来。
那年月,唯一记住的名言是“天生德于予,桓魈其如予何?”“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那年月,唯一读过的古典名著,算是《水浒传》无书可读的知青们打着手电夜以继日地轮着看。
后来,大约是1975年,一本手抄本的小说首先流传到了我的手中——《一双绣花鞋》。它有诡秘、有惊险、有跌宕,有人情,有风物。知青们轮流着抄,分时段读。
那年,在河套地区出差,一大学同学到我住的宾馆探望。见我正读南怀瑾的《老子旁通》,便惊讶地问:“啊,这可咋办呀,毕业二十多年了,你还在干这事?咋就一点长进也没有来来?”
我起初无语,继而辩解说:我呀,就这点爱好,假如连看书也不让了,更没活着的意义了……”
他“唉”了一声,也无语了。大半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可当年的他不是这样呀?
他也算是我的上铺兄弟,一个朴实的农家孩子。记得大三时,宿舍里六个同学,没有谁忙活着要考什么研究生,只有他张罗着,考什么法学呀、古汉语呀。后来大半因为功底或者外语的障碍,不能遂愿,毕业后就回老家教书了。没有教几年书,赶上席卷全国的下海大潮,就提前退休经商了。显然,他的经商天賦远远超过了什么古汉语和外语,早早就成了全班同学“最先富起来的人”之一。再后来传说他也有不一帆风顺的时候,再后来,居然没有消息了。
20世纪80年代,大概是最让人惦念的时代。读书、求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校园里到处是读书的人,树荫下、墙根底,下课排队“领”钢丝面的时候,一人一个小本或卡片,在背诵英语单词或古典诗词。印象最深刻的是中文系77级的钱江师兄。
北京知青,花眼、肤白,儒雅、俊俏。身披一件深灰色的旧呢子大衣,上面似乎刻有岁月的痕迹。从图书馆迈出时,腋下夹着四五本,怀前还捧着两三本。绝对用“风流倜傥”是不为过的。那时既潇洒且会摄影、会唱歌、会写文章的他,注定是女生仰慕甚至暗恋的男人,因为纵使男生也会心生复杂。
1981年,中文系成立过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诗社,叫“未了”。名字着实没有起好,原本是想说“齐鲁青未了”,不料成了谶语,好像不几个月就夭折了。
那时,在校园的空地上,偶尔有艺术系四个人一吆喝,一合计,就来个“弦乐四重奏”,周边围了一两圈来自各系的听众,虽半懂不懂的,却静静地听着。似乎不是为了时髦,而是要为干涸过久的土地吸取一丁点水分,听懂与否倒是其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