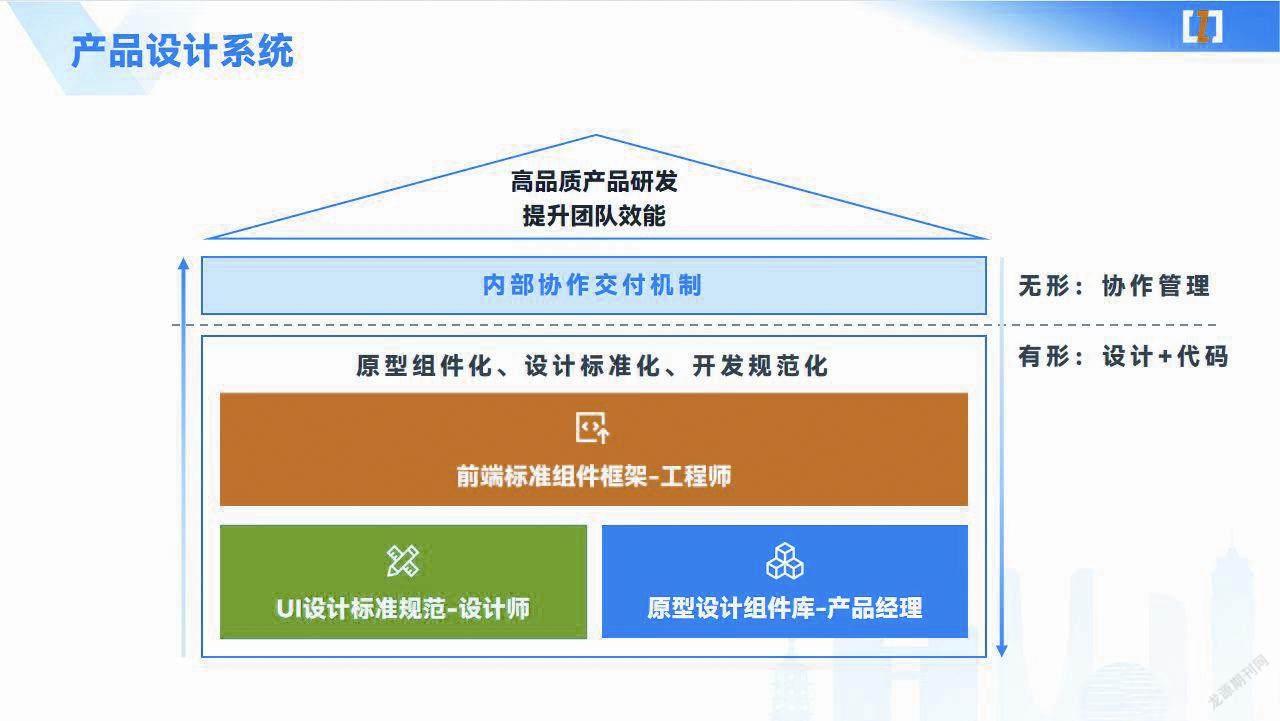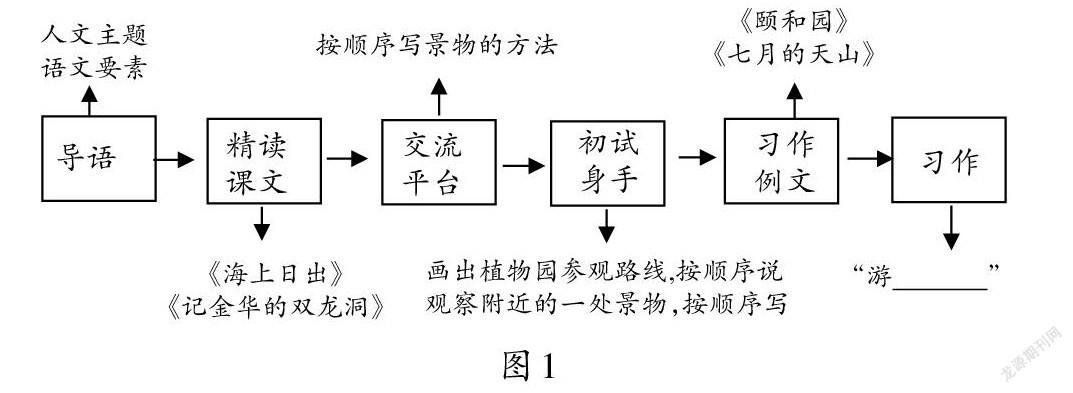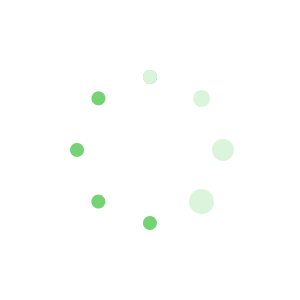摘要:对于双方动机错误的问题,我国现行法没有明确规定。欲知双方动机错误如何适用法律,首先应当确定的是动机错误在体系上的定位。由于我国的现行立法中没有直接出现动机错误一词,《民法总则》中的“重大误解”一词理应包含“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之义,但学界和司法实践界对“重大误解”真正含义存在较大争议,现只能先求助于比较法的立法和学说。学说上通过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二分体系,将动机错误排除在错误规则体系之外,并借助于交易基础制度加以解决。但我国对于交易基础丧失制度的规范不够详尽,诉诸于“重大误解”可能是更好的路径。
关键词:双方动机错误;交易基础丧失;重大误解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6-0077-03
一、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的二分
在德国潘德克顿民法(以下简称德民)体系之下,意思表示错误被分为意思表达上的错误和意思形成上的错误,即错误的“二元论”。此种划分直接来源于萨维尼的意思表示错误学说,其认为意思和表示的不一致是表意人内心意思与所表示的效果意思出现了偏差,意思和表示不一致所产生的错误将导致意思表示无效。在萨维尼的学说之中,动机错误原则上是不重要的,动机错误并不会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
此种对于意思表示的形成表示阶段的严格划分,真正原因在于:意思表示的形成阶段,每个个体的行为和意思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干涉。萨维尼的意思表示错误学说真正为德国民法典奠定了理论基础,一切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都将在其学说的基础上展开。正如弗卢梅评价,萨维尼对错误问题的最重大贡献并不在于其找出了解决错误问题的新方案,而是将错误理论在法律行为制度中得到了贯彻[1]。此后诸如贝克尔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错误与表示以及可归责性理论,均是在萨维尼学说基础上的锦上添花。
与德国民法所确立的错误“二元论”不同,诸如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立法采取错误“一元论”的立场,即不在法律上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两种情形适用相同的规范进行处理。同时随着现代私法的国际统一化的发展,许多国际示范法也开始倾向于“一元论”,比如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其3.2.1條对错误下的定义为,错误是指对于合同成立时存在的事实或者法律的不正确假定。由此看来动机错误属于该种所谓“事实错误”的调整范围之中[2]。
针对德国传统错误“二元论”的观点,学术界对其弊端的批判从未停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具体错误类型的划分意义不大并且界限模糊;(2)不断通过立法和判例创设特殊规定将动机错误纳入调整范围,实际上的体系一致性开始变得杂乱;(3)许多特殊的错误,如法律效果错误、计算错误、性质错误与同一性错误,难以界定处理[2-4]。而正是意识到了潘德克顿体系下错误“二元论”的弊端,许多德国学者也走向了“一元论”的立场,比如蒂策完全否认表示错误和动机错误的区分具有法律相关性,其认为当表示相对人意识到错误、表示相对人致使错误的发生、表示相对人在错误表意人主张错误之前尚未基于表示进行任何处罚时,任何错误都值得关注[1]。
回到我国现行立法上,《民法总则》(意见)第七十一条对“重大误解”的解释如下: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此种界定似乎不能与德国错误“二元论”中的表达错误等量齐观;同样其是否采“一元论”观点将动机错误纳入调整范围,也缺乏有力的佐证。既然通过法律解释无法确定“重大误解”真正含义,本文试图在现行法框架下,借助双方动机错误这一问题,在解决其法律适用问题的同时,探究立法者对于“重大误解”的真正定义。
二、双方动机错误与交易基础
在错误“二元论”体系下,原则上动机错误非属于错误规则调整范围,但通说认为双方动机错误属于例外情形[5]。双方动机错误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通常以特定的、现实的或者将来的情况为出发点[6]。与赋予当事人撤销权的单方错误不同,双方错误排除撤销权,因如果双方都具有撤销权将导致法效果完全取决于“偶然事件”,即谁首先行使了撤销权并将因此负有赔偿信赖损失的义务。同时如果赋予受有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撤销权也是相当不合理的,因其须对相对人负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其较能兼顾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解决方法,系依诚实信用原则调整当事人的法律关系[5],德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当适用德民第313条的规定。
德民第313条即为所谓的交易基础规则,其中第1款规定的为客观交易基础,包括权利义务关系失衡、经济上的不可能、目的障碍;第2款规定的为主观交易基础自始丧失,包括在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认识错误,而对方当事人自己没有认识而无异议地接受了,从而构成了双方动机错误;第3款规定的为法律效果[7]。值得一提的是,此种客观与主观交易基础的划分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比如梅迪库斯认为,无论在主观交易基础还是客观交易基础中,当事人都存在不正确的判断。此外即使在主观交易基础中,仅有错误本身不足以认定交易基础受到了干扰,仍需具备履行的不可合理期待性这一要件[8]。
认定交易基础障碍的本质性标准在双务合同中主要是等价遭到破坏,当然还有其他因素:(1)考虑实际情况的可预见性(例每年的货币贬值);(2)考虑到当事人约定的给付目的(例适当的供养);(3)双方合同当事人具有重要性的事由也具有意义(例双方动机错误)。此外,还有两个容易产生误导的因素:(1)个人的给付能力的区别不影响风险分配;(2)合同是否履行不影响交易基础的认定,特别是对于已经履行的合同,仍可能适用交易基础制度,因为受到现实情况损害的当事人已经履行了他的给付义务之事实,与他应该获得何种对待给付的问题是毫无关联的。最后,交易基础适用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双重的规定漏洞(法律行为内容以及法律规定),如果法律行为或者法律规定已经包含了某一风险事由的约定或规定,那么就不存在需要由交易基础学说来填补的漏洞了。
双方动机错误分为对既有事实的认识错误以及对将来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产生的错误,前者为交易基础自始不存在,后者为所谓客观交易基础,即交易基础事后丧失中的目的障碍。如此分类方法将导致在继续性合同中,同为双方动机错误而出现两种不同的法律效果,前者将导致整个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后者将导致向后的变更或者继续性合同的终止[8]。
由上述可知在德国错误“二元论”的体系下,双方动机错误并非在错误制度中予以调整,而是依据交易基础制度进行调整,同时对于双方动机错误更有进一步的划分。双方动机错误的法律效果并非首先是解除合同,而是针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要求调整合同请求权,要么是要求依照变更了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第313第1款),要么是依照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第313条第2款)。只在调整合同为不可能或对于一方合同当事人为不可合理期待时,遭受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才可以解除合同[9]。
与“二元论”不同,在“一元论”的框架之下,由于并不区分对待动机错误,其当然属于错误制度的调整范围,法律后果是双方当事人均有撤销权,而未另行创设制度对双方动机错误进行调整[2]。于我国现行法体系下,尚不存在德国之交易基础制度,似乎可以得出我国错误制度应为“一元论”,否则如认为采“二元论”,将会出现法律漏洞,对于双方动机错误无可适用之交易基础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情事变更规则,实际上就是德国交易基础理论中所谓的客观交易基础丧失,但并未规定自始双方动机错误之情形。许多持“二元论”解释“重大误解”的学者,对于双方动机错误倾向于类推适用该条之情事变更规则。
三、我国双方动机错误的法律适用
在尚不确定我国“重大误解”究竟采用“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的前提下,不妨分别依两种路径进行实证推论。现在假设“重大误解”采错误“二元论”之立场,“重大误解”仅调整表达错误以及其他诸如性质错误等特殊情形,至于双方动机错误则无法条适用。如上文所述,此时双方动机错误似乎应当类推情事变更规则,即《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其法效果为双方可请求变更或者解除。
在双方表达错误的情形下,按照“二元论”之立场应当首先直接适用“重大误解”,其法效果为双方均享有撤销权。由于我国与德民122条之无过错缔约过失责任不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撤销人将承担有过错的缔约过失责任,不会导致先撤销一方承当不利益[2],无需另外构建交易基础制度来解决德国之“偶然事件”问题,更不必类推情事变更。
从法效果上观察,双方表达错误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双方当事人仅拥有撤销权,这将导致其法效果上较双方动机错误缺少变更的机会。然而双方动机错误的的瑕疵较双方错误的情形更轻,但法律对其之优待却更大,显然不合理。
此时有三种解决途径:(1)双方动机错误同双方表达错误一样仅有双方撤销权,此种处理方法实际上肯定了“重大误解”采“一元论”,本质上将会走向一元论;(2)双方表达错误與双方动机错误一样具有变更权,在《民法总则》尚未颁布之前,《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重大误解”的法效果确实包括变更权,但是立法者于新法中将其删除,说明采取此种做法将有违立法目的;(3)双方动机错误仅具有撤销权,而双方表达错误具有变更权,此种解决方法在现行法上因无法条依据而无法展开,故不采纳。
再假设“重大误解”所采乃错误“一元论”之立场,任何错误均统一适用重大误解,但是由此导致双方均有撤销权是否需要例外处理?德国因此构建出交易基础制度,而我国则仅有交易基础制度中的客观交易基础,无其他交易基础丧失的相关规定。如上所述,我国无需如德国规定双方错误可撤销的情况下适用交易基础制度,因我国为有过错的缔约过失责任,不会导致先撤销一方承当不利益,通过撤销的途径已经可以很好保护双方当事人,无需另外赋予双方当事人变更合同的权利,民法总则中删除变更权与此一致。
综上所述,如认为我国之“重大过失”采错误“二元论”,则无法协调现有法律规范。采“一元论”不仅能够很好地在现有规范中解决双方动机错误,且与立法意图相一致。
四、变更之移除与“重大误解”之含义
变更常被解释为撤销且另行形成意思表示,并将其作为撤销的一种特别形态。此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合同法》五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之规定将变得不可理解,在其解释之下法律行为撤销本就是变更权的效力之一。朱庆育认为该款的规定显然意在维持既有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理解为在维持既有法律行为效力的同时,变更其内容更为恰当[10]。但如此解释,变更权意味着仅凭一方的意思表示既可以变更双方的合同,完全属于对意思表示错误的矫枉过正。
《民法总则》将变更删除的原因来源于梁慧星所提出的修改建议。其认为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在撤销权之外所赋予变更的效力,可解释为附着于撤销权的另一项形成权,即“变更权”。此项变更权之行使,将依权利人单方的意思而变更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使权利人单方的意思具有拘束对方当事人的效力,有悖于《民法总则(征求意见稿)》宣示的“平等原则”(第三条)、“意思自治原则”(第四条),有悖于民事法律行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双方合意不得变更的基本原理,显然属于矫枉过正[11]。
立法者采纳了学者所提出之建议的原因在于,“变更权”之效力仅凭一人即可发生,将会严重影响相对人之意思自治,但存在例外,如《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所规定之情事变更,即使在及其尊重当事人之意思自治的德国体系下,情事变更亦属于例外可变更之情形。由此观之,立法者删除与《民法总则》“变更”,有严格限制“变更权”适用情形之意图,即不可任意扩大现仍存立法中“变更权”的适用范围,如仍认为双方动机错误之情形可类推适用情事变更之规则,实与立法目的相悖。
根据上一节之论述,通过与双方表达错误之间的利益衡量,双方动机错误在现行法下不应类推适用情事变更规定。此外,如类推适用情事变更规则还将与立法者删除“变更权”相矛盾,如不当扩张“变更权”之适用范围,实与立法目的相悖。双方动机错误和双方表示错误在现行法下均应直接适用“重大误解”的相关规定,而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中所规定的“重大误解”一词理应包含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重大误解”一词应当作错误“一元论”之解释,但仍需继续考察研究其他与错误“一元论”相适配之规定是否存在。例如,“相对人可识别性要件”[3],否则《民法总则》一百四十七条将存在调整错误范围过宽之嫌。
参考文献:
[1]弗卢梅.法律行为论[M].迟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韩式远.合同法总论[M].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3]李俊青.民法总则重大误解视野下动机错误的救济路径分析——以错误“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为切入点[J].法学论坛,2017(11).
[4]梅伟.民法中意思表示错误的构造[J].环球法律评论,2015(3).
[5]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吕特斯,施塔德勒.德国民法总论[M].于馨淼,张姝,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7]罗歇尔德.德国债法总论[M].沈小军,张金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8]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9]施瓦布.民法导论[M].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0]朱庆育.民法总论[M].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1]梁慧星.《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解读、评论与修改建议[DB/OL].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x?id=4736.
作者简介:龚杨帆(1995—),男,汉族,江西南昌人,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