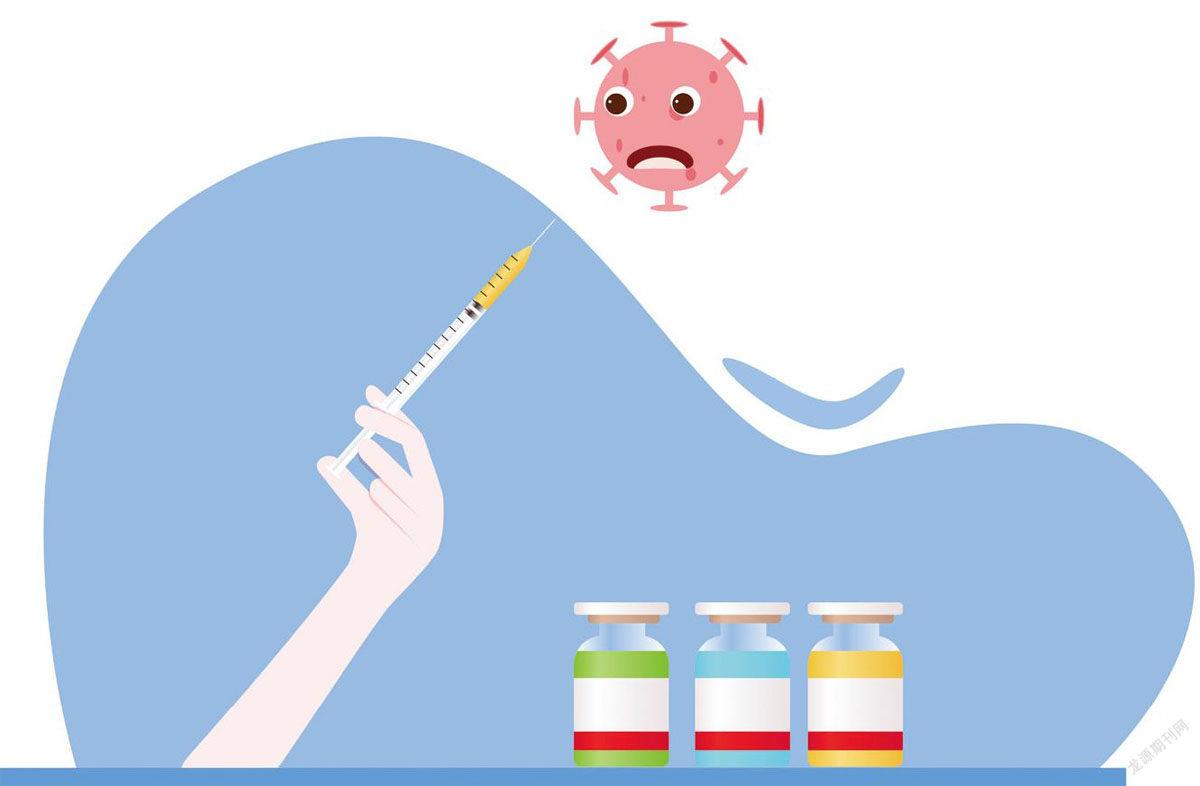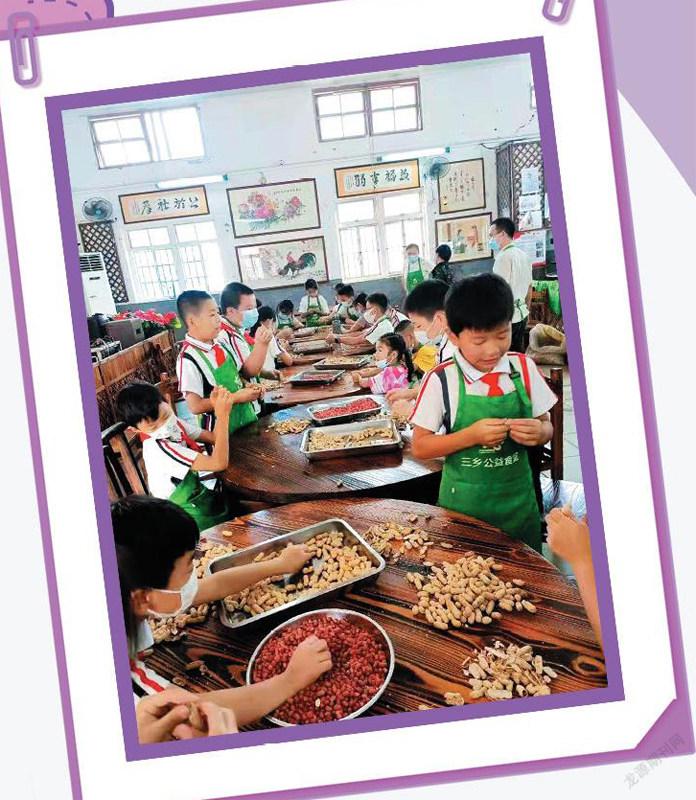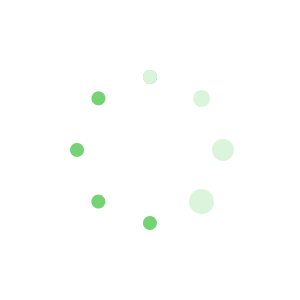曹恺 杨小彦 吴毅强
曹恺:终端的历史意象
“终端”这个词来自计算机系统。大概在1995-1997年,我使用过SGI工作站,运行的Unix系统是相对比较专业的编程语言,我当时使用的终端是一台台式计算机的显示屏并外接两个电视监视器,形成一个三屏的工作区。到今天为止,终端的形态和意义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尤其是我们在一个当代艺术的语境里面来讨论终端,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它的意象。
终端的第一个意象,是计算机信息抵达人类的一个终点站,就像它的英文“Terminal”的意思,是一个抵达点、终点站的概念。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我们人类接触外部世界的终端就是我们的感知器官——我们的触觉系统、视觉、听觉和味觉系统。而影像从机械传递到人,则是通过播放这个方式,形成一种人和机器的交互。从影像角度来说,影像的终端,就是抵达观看者的界面。
从机械文明概念来说,电影终端是我们人类和机器相互感知的第一个终端。我把它定义为“一束光、一块布或一面墙”。对电影概念的解释有多种多样,我觉得最深刻也是最简单直接的说法,还是已故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周传基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电影就是“光和声音”,这涉及了电影最本质的系统。今天我们暂时不讨论声音的部分,我们讨论光。电影是光通过一面墙上的一块布把它的信息传递给我们。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是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1895),在这之后,有很多人模仿过火车进站这个场景,把这个意象传递给我们,这代表电影抵达人类的一个终端。它驶进来,它也抵达了。
随之而来的,是电视作为一个终端出现我们面前。电视机和监视器之间的区别,就是电视机多了一套接收系统,它通过无线、有线等各种方式,来接收信号。它传递信息的基本技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显像管,也就是阴极射线管(CRT)。监视器则是通过一个AV端口和录像机进行连接,我们才能够观看。电视机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但是它真正的普及是在二战之后。当时,电视终端提供给大家的仍然是一种类似于家庭影院的雏形,也就是说,在影院模式之外,它开创了一种家庭模式或者说个人接收模式,而影院的接收系统仍然是一种集体模式。
但是对艺术家来说,任何媒介都会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工具。就像电影发明以后,它很快促生了“实验电影”这一艺术门类。电视也很快就被艺术家所使用,比如录像艺术的先驱白南准和他的太太久保田成子。作为录像艺术家,他们当时就开始直接把电视机终端作为展览的一种影像现成品,把它放到展厅里面去。这时也出现了最早的“录像雕塑”,比如:白南准大量的电视机堆砌,或者是按程序排列的电视机阵列,等等,呈现为一种机器乌托邦的存在。录像艺术的开端,可以与终端的外延关联起来。
从电影放映机到电子模拟投影仪,我把它们总结为两种不同获得的影像:一种是正面投影,一种是背投。就像我们早年看露天电影,你可以从正面观看,也可以从反面观看,只不过反面得到的是一种镜像的图像。其实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数字投影仪,就是在模仿和延续电影放映机的工作方法,也包括背投电视机,它们一正一反、互为解释。
电视机作为一个终端出现得比较早,而计算机要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个人电脑的发展才逐步普及开来,到今天成了我们最基本、最常规的一个终端。计算机终端和电视终端有很多共性,也有很多差异。计算机终端连接的是电脑主机和键盘,后来添加了鼠标,它有一个互动关系。电视机终端只有接收和播放的功能,缺少互动的功能。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今天已经从电子模拟时代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时代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大。在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超大型的、3D環幕的露天大屏;
而它又可以小到我们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样的微型终端。
随着终端变化而来的是观看模式的改变。一种是“剧场模式-电影院-录像厅-家庭影院”的变化,剧场模式自电影产生以来,有了胶片,然后出现了电影院的概念,成了一套系统。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能看到它延伸出来录像厅和家庭影院这样的系统。另一种是“美术馆模式-画廊和替代性艺术空间”的改变。终端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我认为:终端的终极意象还是会回归到人的终点和机器的终点相遇的交汇点。它更多产生于一个传播和接收信息的系统,对此,更多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杨小彦:从分格走向运动——迈布里奇、马雷、杜尚与培根的意义:静止图像的崩溃
我今天是来讲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摄影制度的崩溃。
摄影界一般很少讨论迈布里奇(Eadweard J. Muybridge,1830-1904),因为通常把他看成是一个科学实验的先驱。但是问题没那么简单。
一切都归结于我们的眼睛。人眼是感受运动知觉的器官,但是在摄影术出现之前,没有一个物理存在(如照片)能证明它。因此,“真实的瞬间”就是一个假设、一种想象,对瞬间的表达只能让位于艺术,比如绘画。摄影的出现,把时间如同切片,一片一片地切下来,我们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瞬间,也证实了希腊著名的芝诺悖论(飞矢不动)。摄影使瞬间成了眼前的事实,最经典的呈现就是迈布里奇在19世纪所拍摄的一系列分格照片。当时,迈布里奇受到美国铁路大亨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的委托,去做一个重要的实验。马在飞奔的时候,是四蹄腾空的吗?籍里柯1821年的绘画《埃普松赛马》是这样描绘的。到了1877年,迈布里奇应斯坦福之邀,为他的奔马拍摄了连续的分格照片。通过两次拍摄的实验证明,籍里柯笔下的跑马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在跑动时总有一只脚踏在地上,而不是四蹄腾空。
中国东汉的青铜器《马踏飞燕》也有一只脚踏在地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很有智慧,很早就意识到了马在飞奔的时候并不是四蹄腾空的。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前蹄是一起向前一起向后的,这也是不对的,因为马真正跑起来是前后交错的,更何况它的主题是“马踏飞燕”,当然会有只脚在地上。事实上,中国古人也认为马跑起来是四蹄腾空的,比如之前出土的一个唐代陶俑,一个女性打马球俑,马的四蹄也是腾空的。所以说,人类的智慧超不过技术的发展。
迈布里奇后来继续他的实验,拍摄了各种各样的分格照片,有人体的,有动物的。在电影出现以前,这样的分格照片是非常奇妙的景象。这时,迈布里奇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让分格照片动起来,如何来呈现运动的状态。物理学家普拉托发明的费纳奇镜(Phenakisticope)给了迈布里奇一个重要的启示,促使他发明了运动视镜(Zoopraxiscope),后来这个发明又启发爱迪生发明了电影放映机(1889年)。另外还有一个人,是生物学家马雷(Etienne-Jules Marey),他在迈布里奇的摄影实验之前,就写了一本关于运动结构的书,预言马在飞跑的时候,一定有一只脚在地上。马雷一生都在研究各种各样的运动,1882年,他研制了一支摄影枪,1秒钟可以自动开启快门12次,用来跟踪拍摄包括飞禽在内的各种动物的运动姿势。卢米埃尔兄弟发明摄影机以后,马雷马上参照发明了高速拍摄(60/秒),以便让运动在呈现时慢下来(慢镜头),从而把运动分解得更加精确。从技术上来说,马雷的摄影枪和迈布里奇的连续摄影的思路刚好相反。迈布里奇通过多部相机依不同时间分别曝光来获取运动图像,马雷则在一张底片上通过镜头追踪(12/秒)去再现运动本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是两端发展的结果——迈布里奇的分格照片如何呈现,启发爱迪生发明了电影放映机;
卢米埃尔兄弟受马雷影响,导致的是电影拍摄机(活动电影机,1895年)的发明。这两端都不能少。
活动影像的出现对艺术家的刺激非常大。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杜尚,他1912年画的《走下楼梯的裸女》就直接受到了多重曝光的影响;
另一个是培根(Francis Bacon),我们看他的肖像系列,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在画一个对象。其实培根一直在琢磨迈布里奇的分格照片,可以说,如果没有迈步里奇的摄影,就没有培根。从某种意义来讲,培根是针对摄影在创作,对他而言,摄影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也是一种重大的启示。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摄影干掉了绘画,图像代替了世界;
同样,电影统治了视觉,活动影像遮蔽了运动知觉。
吴毅强:后媒介、屏幕、物质性、表面
我今天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后媒介时代:从惯例到剧场”,我们看艺术,从以前重视品质的惯例到现在更重视剧场的效应;
另一个问题是“屏幕”的问题。
我最近在看美国艺术批评家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的《北海航行:后媒介时代的艺术》(A Voyage on the North Sea:Art in the Age of the Post-media Condition),她讲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媒介时代。怎么来理解她这个说法呢?从艺术史角度来说,我们知道它经过了三个时期:古典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时期或者叫当代艺术时期。对媒介特性比较注重其实发生在现代主义时期,尤其是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提出了现代主义绘画的媒介的问题。随着后现代、当代的到来,我们今天不再是纯粹地去追求单一的媒介属性或语言和美学形式。就像前面大家讨论的那样,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终端去进行展示,绘画都可以进入到终端里面成为一个局部。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研究摄影,还是电影,都很难只从它的本体语言去进行研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媒介混合的时代,一个后媒介时代。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列了一个大概的阶段的变化,从现代主义绘画到影像艺术,中间经历了一个极简主义阶段。极简主义其实是两个阶段之间的一个过渡,它非常重要,没有它的话,我们就无法从以前传统的单一媒介,比如绘画、雕塑、建筑等,过渡到今天。艺术几乎无所不包。今天是一个异质性和混杂性的时代。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先来看波洛克的绘画《1948年第1号》,现代主义绘画追求什么?用格林伯格的话说,是媒介的单一性和纯粹性,就是说它是要把媒介的可能性穷尽到极致。为什么大家不再画具象绘画,因為那是一个错觉,不是一个真的绘画的平面,它没有重视绘画本身的问题。所以只有在将绘画不断地往平面化推进、不断地走向抽象的过程中,我们才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绘画,而不是一个错觉的、三维的空间。再往后,我们看诺兰(Kenneth Noland)的《Ado》(1967),他的所谓的色域绘画,进一步走向极简和纯抽象,他所追求的,不再是之前我们看到的点、线、面的东西,而是在探讨绘画的边界问题。也就是说,这时候的艺术家越来越重视艺术的物理特性,越来越重视媒介本身。慢慢地,他们考虑的不再仅仅是我到底做了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这个东西,它跟墙面、跟空间、跟它的媒介属性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从以前的绘画的惯例,进入到一个剧场效应。就像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提出的“剧场性”这个概念,他认为:现在的艺术从以前我们凝视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跟观众发生关系的事情。现代主义根本不重视观众,观众算什么。但今天的艺术,交互艺术也好、终端的交流也好,几乎没有不重视观众的。
到了影像艺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之前的观看习惯,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异质性的东西,我们很难说它有个什么媒介的本体属性。我借用一下摄影评论家约翰·塔格(John Tagg)的观点,他说今天的摄影其实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刚才曹恺老师讲了很多物理的终端,但这些是纯技术的东西,也许并不能反映摄影或者录像本身。所以约翰·塔格说摄影本身是不存在的,它一片空白,但它可以承载所有的东西。或者说,只有影像这种媒介它是不呈现自己,而是呈现别的,这种特性使得它的传播和接受变得多元。
接下来我讲一讲屏幕,屏幕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都在研究屏幕反射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太多地去研究屏幕本身。我们认为屏幕是多重空间的一个交接点,是一个视觉艺术。比如做演讲,这个投影作为一个光信号或者视觉信号,它跟现场的这个空间是在发生关系的,换言之,屏幕本身就是一个相遇、混合的场所。这也是它的异质性所在,这也关系到屏幕本身的物质性。屏幕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还涉及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合,包括视觉艺术、建筑、摄影、录像等,都在它的表面呈现,形成了所谓的表面张力。它把很多意志的东西,在瞬间通过一个统一的信号传达给我们。今天的屏幕不是在纯粹地反映图像,而是作为一个隔断,或者说,它如同一个中介,去进行了转化。这种转化对我们的印象和记忆都会产生改变。屏幕是流动的。柏拉图的洞穴理论,讲到囚徒从面前的墙壁上看到的流动的影像。在今天,这种流动的影像渐渐演化成屏幕。走出了洞穴,我们和屏幕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论是投影还是那块墙壁,它们都在不断地构建新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切割我们生活的空间,改变着观者。
最后我想提出来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这么多的终端,这么多不同的显示材料和机器,互联网、车联网、人机互联,什么都可以进行联结。反而更凸显了我们人精神的困境,正所谓万物互联、众生孤独。屏幕确实带给了我们方便,但也使人对其产生强烈的依赖和焦虑。在今天,我们如何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
自由讨论
孟尧:这次的“XPM影像学术论坛”,上半场“影像生产的区域生态”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的分享,下半场则有些烧脑,3位嘉宾的发言信息量非常大,涉及媒介的变迁、艺术史和传媒史的关联等。刚才各位嘉宾讲的点,有些还没有展开,可以再谈一谈。观众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问。曹老师先来说吧。
曹恺:我觉得刚刚我们三个人讲的串联起来,正好是一部影像发展史。杨小彦老师前一部分是讲的从动态影像走向静态影像的发展过程,而且有各种丰富的图例图示,通过一些历史上的具体案例给我们分析得特别细。杨老师最后讲的实际上是他演讲的华彩部分,讲到影像和绘画之间的关系,这个就体现了他综合性知识结构上的优势,他的跨界的类比,从中提炼出的观点我感觉非常新鲜;
我实际讲了从技术衍生到与艺术史的关联,其实从影像艺术史发生发展的过程来说,它始终是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往前滚动的,它始终依附于科技进步的历史。如果脱离了技术背景的参照,单纯来谈论它,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无根可依;
吴毅强讲到后媒介的关系,他从极简主义延伸到影像,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独立思考产生的观点。
实际上我对马海蛟的作品《如果把绿色删除,如果开始关心植物》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绿幕背景是影像生产的一个特殊的技术背景,它主要用来抠像,而在今天,它的内涵被进行了延伸,我已经看到有好几个艺术家的创作包含了对绿幕的观察。所以我想问一下马海蛟,从影像的生产到终端的呈现,你对这样一个过程有什么样的思考?
马海蛟:作为一个影像创作者,我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首先是想到绿色這个元素,然后才延伸到它作为一个技术条件跟影像的关系。对我来说,这里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拓展,技术条件作为一个出发点,会给创作者带来一个无限联想的契机。所以从艺术家联想性的想象出发,我们可以更“为所欲为”一点。我觉得艺术家有时候需要知识,需要一些历史背景的摄入,但作品本身还是要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意味在里面。我想把这个技术条件用我个人的语言去消化掉。这是我个人工作的一种方法。
吴毅强: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是通过笔记本电脑来观看马海蛟的这件作品的。我觉得这种终端只能是一个替代品,肯定不是艺术家想要展现的方式。其实终端的改变会产生很多误区和歧义,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我们的知识系统和信息必然是不完整的。关于这一点,我也特别想知道孟尧你的观点。
孟尧:今天我们谈到的终端,其实指向的都是电子终端,比如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以及今天现场的投屏。这里就衍生出一个问题:终端展示的方式如何影响传播。我想到一个词,叫作“尺寸可变”。尺寸可变意味着在不同的场域、针对不同的空间、相异的展厅条件,艺术家对于自己创作的内容如何呈现是有不同要求的。在美术馆和各类艺术空间如何呈现自己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创作者在具体的展示环境中的传播诉求。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请董钧聊一聊,你是如何处理作品与展示现场的关系的?
董均:2020年我的新个展“两生花”有两件影像装置,是完全为那个展厅定制的。我会和展览空间设计阎洲一起根据展厅具体的空间尺度去设计展览方案,所有影像作品的尺寸和装置的关系都是经过反复地推敲,然后再回到现场去做一比一的模拟,去感受。前段时间去杭州看了丁世伟的新个展,他这次使用的是全世界最小的屏幕,同时他把LED显示屏进行了不规则的切割,这里的屏幕已经不是我们常规的形态。曹恺老师早年做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是一个传统的黑盒子放映模式,观看是神圣和严肃的,影片放完字幕大家开始鼓掌,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观看。而美术馆的“白盒子”系统里的影像,大家是可以随时进来、随时离开的,观众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时间感受作品本身。再到手机这种小屏观看模式的时候,它就完全碎片化了,又具有很强的交互性。终端和屏幕的变化,不断地在调整我们观看和进入它的可能,未来可能会变得更有意思。
杨小彦:我们都是影像的实践者或研究者,今天主要是讨论终端的变化。我想从传播学的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传播技术决定知识形态。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被屏幕控制了,我们处在一个传播碎片化的时代。我们不断地接收新的信息、不断地去浏览。谷歌每一秒钟可能有上百亿次的访问。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终端,每一个人都备受考验。我们干不过大数据的记忆。而在知识碎片化的同时,我们还一个深度链接的存在。只要你愿意,你不需要老师,通过无穷链接,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专家。二者结合,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传播环境。
孟尧:2019年我在《画刊》策划过一期特稿《在屏上》,我邀请了一些艺术家和策展人,请他们从自己的手机上选取一张截屏图片,并以这张截屏为主题写一篇文章。“截屏”是我们日常使用电子终端的常规动作,但截屏那个瞬间的选择和状态实际携带了很多信息,这个动作背后反映的是截屏者某一瞬间的想法与需求。今天我们在谈终端的时候,实际谈的是身体和机器的关系,是屏幕、技术和人的关联。前面马海蛟的演讲里提到一个网络流行词“恋屏”。它很好地概括了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日常状态,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屏幕上。尤其快手、抖音这种短视频平台兴起以后,这种刷屏生活就更高频了。所以在今天,手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传播媒介,它还是我们身体的延伸,甚至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器官”。我想问一问矫健老师,你是以传统的摄影媒介做创作的,今天这种屏幕生活对你有哪些刺激?
矫健:我正在想一个问题,应该刚好也能对应于这个话题:“终端”这个词,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有时候更像动词,而显示器也不仅仅是一种承载体,它的作用在日常交互或者生产的过程场景当中,像是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参与者,是活的……我上午发言中介绍学院样本用了“实验”这个词,意味着我们对于技术发展的思考和态度,这种演化中的技术与艺术应该是自然、有机地混杂在一起的。就我个人的创作而言,这一切我都会尝试,我会选用一个我认为合适的“还可以”的东西,虽然我常用传统媒介但不拒绝所有的技术,实际上是不是用这个或者用那个(媒介)现在不拘泥。创作,有时候就凭“一时兴起”。
观众: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作为一个学生、一个年轻人,我在做作品,甚至仅有想法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顾虑,我会怕你们觉得我们很幼稚,觉得我们很多想法不成熟。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会影响我最初的想法和开始在做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做的东西很幼稚呢?
曹恺:年轻人是允许幼稚的,如果到我们这个年龄再幼稚那就不对了。有想法就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在各个年龄层呈现出来的创造的方式和形态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若干年后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的作品,你会发现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确实有幼稚的这一面。但这恰恰就代表你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年龄,它所产生的一个真实的结果。任何时候,我觉得你把影像存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是递增的。你们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认识,不要轻易地放过自己的想法,让它只在萌芽状态就被消灭了。
矫健:关于这个我有话要说,学生担心自己做的作品或者想法幼稚,我倒觉得没有问题,没必要担心。在我这,“幼稚”不是贬义词,话说我们想要“幼稚”也“幼稚”不起来了,哈哈。这个“幼稚”是最天真、最纯粹、最可爱的东西,你就做“幼稚”的作品,我觉得就真诚,就对了。要不然你现在不幼稚,什么时候幼稚?想要伪装成熟是不对的,没道理的,天真和幼稚的气息就叫作学生气,在你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那你也没有未来,所以我们就坦然做一个“幼稚”的作品吧。
董钧:其实有时候为影展选片子,会很偶然地看到那些技术很糙但很有力量的作品,那种原始的感受力实际反而更打动我。现在太多被建构的、当代艺术新八股的套路化的那些东西我们看太多了,它丧失了那种扑面而来的敏锐和感动。所以其实你不要怕幼稚,更不要一开始就装模作样地去建构出来一个看似精致得很套路化的样式,那个反而是要警惕的。
注:本文根据2021年3月28日于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举办的“XPM影像学术论坛”现场录音整理而成,文稿经发言人审定,分2期于本刊发表,上篇参见《画刊》杂志2021年第4期。
责任编辑:姜 姝
猜你喜欢 媒介终端摄影 高清大图旅游世界(2020年7期)2020-07-28联通5G CPE:为终端提供5G接入能力通信产业报(2019年31期)2019-10-21辨析与判断:跨媒介阅读的关键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5期)2019-05-28高中语文跨媒介阅读内容的确定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1期)2019-05-28论媒介批评的层面文艺生活·下旬刊(2017年4期)2017-05-27“吃人不吐骨头”的终端为王销售与市场·渠道版(2017年2期)2017-03-09完美终端商界(2016年11期)2016-11-30完美终端商界(2016年11期)2016-11-30声音的“邮递员”好孩子画报(2014年7期)2014-08-13最美的摄影焦点(2014年3期)2014-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