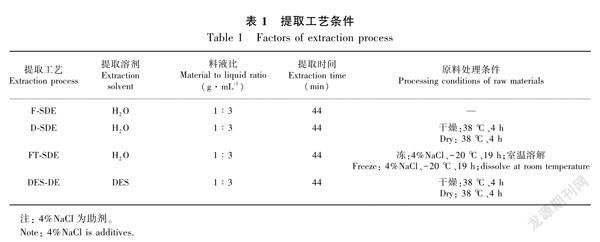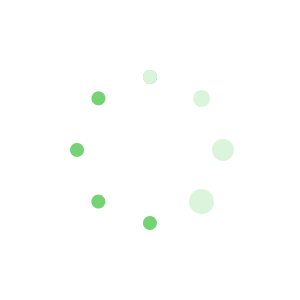“如果想要寻求谎言,却找到真相,这是太过高昂的代价。”这句话来自小说《审查官手记》,作者是葡萄牙人洛博。安图内斯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人,安图内斯在这句话后,接着写:“请你们像梦中一样在我的篇章里行走,因为只有在这场梦中、在梦中的光明和阴影中,你们才能找到小说的意义。”准确地说,我并不想把这五个发生在夜晚的故事,包装成虚构或真实的样子——两样都没什么意义。因为很难说。或许,情节和故事像真实和虚构一样,只是托词。我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想说什么,和你们因此想到什么相比,一点也不重要。请你们有机会告诉我,你们想到了什么。下面让我来把自己知道的,全告诉你。
一
第一个说的是一个叫小韦的人的事。据我所知,这人的爸爸年轻时在乡下靠小偷小摸过活,后来偷电缆时被电死了。我见过几次小韦妈,一个极普通的妇人。外人这么说他爸爸也就算了,小韦也去问过他妈妈。每次,小韦妈都会变得暴躁起来:
“去他妈的净瞎说!偷公家能算偷?那年头谁不偷?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当时,他们家的生活的确不好,他爸死后,就更差了。小韦跟他妈长大的过程很艰辛。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格外尊重他妈的看法,比如说在处对象一事上,他的习惯是,感觉差不多了,先跟他妈谈谈,大家再见个面,事情才往下走。
小韦和女朋友小郑商量好,准备明天下午,大家见个面。他们是在一个朋友的朋友的生日会上认识的。朋友的朋友的女朋友和她是闺蜜。看样子她平時不怎么喝酒,也许是现场气氛好吧,她端着酒杯,无所适从地喝了点。那次,朋友的朋友的女朋友,特意制造机会,让小韦送小郑一程……
按小韦的习惯,见面前的那个夜晚,他要和他妈妈谈谈。
“从旅馆窗口,望出去,是波澜壮阔的江水。我们坐在旅馆的房间里对峙。她求我放了她!我笑着走了过去。”
“妈,你猜我后来做了些什么?
天慢慢黑了,他妈妈打开了灯。
“我们第一次见是在KTV里,很吵,过生日的人是谁不重要。大家特意安排她坐在我边上。离开KTV时天已经黑了。我问她家住哪里,说真的,我开始还真没动她的打算。我们晃晃悠悠地,走在夜路上。她忽然小声说,今天本来说住闺蜜家。突然回去,爸妈肯定问东问西。我们在夜路上一直走,走很久。我在超市门前让她等一会儿,买了两瓶水。给她的那瓶,她拿了一路。都是我在喝,喝完一瓶时,她手上还一直拿着那瓶。我看着她,说喝吧,又没下药!她说,你渴就喝,我不渴,帮你拿着呗后来到了江边。妈,我觉得好运临头了。江边旅馆的房间,只有一张床。我俩坐在床边沉默了一会儿。男孩该主动一点,就这样凑合一晚吧,我说。她说每天都要洗澡才睡得着。那去洗呀!她害怕。我在浴室门口当门卫。床很大,我们在中间放了个枕头,然后关了灯。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的朋友的女朋友的八卦。我的手在黑暗中,跃跃欲试。她的手很长,我在黑暗中触碰到了她的手腕。小把戏最终得逞——手指勾住了她的小指。她没什么反应。我转过身,亲了她一下。她躲开了。你不相信我她说,相信啊!问题出在第二天。她抱着我说,她爸真是个小偷。我以为是玩笑,就说没事没事,我爸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他只偷公家。你相信吗?她说,相信啊……”
也是第二天,也就是小韦带小郑来家里的那天。小韦妈不在家,早早出门办事,下午小郑来了,就坐在屋里等,一直等到天慢慢黑了。
小韦有些不好意思,打开了灯,跟小郑说:
“昨晚跟我妈谈过了,你放心吧。”
后来,小韦与小郑的故事,还出现了很多曲折。小韦妈那天去找了当年他爸的情人,那女人的确也有个女儿,不过他们不像你想的那样,就此别过。天底下的事没那么多巧合,顶多是相似而已..不过,还是算了,好运会降临的。
嗯,会降临的。小韦想。
二
第二个事像一场梦,至今回忆起来,脑子还发懵。所以,我把它叫《夜梦》。
2013年冬天,一天下午三点多,我走下公交车。当时挺冷的,我确认了一下表,插兜前行,不远处是大海。走着走着,忽然有个女人冲到我面前:
“对不起,你见过这人吗?
一副焦急又有些无奈的模样一至今我也并不太理解,这个表情代表什么,以及她从哪里来更直接一点就是,这人为什么非来问我?当你环顾四周,当然也可以理解。黑夜即将降临,海潮翻涌起伏的海边,一个人也没有。
我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这个女人看上去挺正常。谁知道呢!这么冷的天气,正常人谁会跑来海边!
远处一道银白色的海岸线,伸向海湾深处。我看了那边一会儿,眼睛就有些疲倦了。刚才我还站在一块礁石上,现在也已经走了下来,海滩上的沙子,踩上去沙沙作响,韧劲十足。站在礁石上时,吹在脸上的风更大更冰。从这个角度望过去,才觉得这里很小。小小海湾,除了海水,从沙滩走上去,只有一条沿海公路,路再上去一些是一些疗养院、旅馆、饭店、招待所、商场。这个季节,几乎所有地方都关门了。从那些乱七八糟的桌椅、停着的汽车,还有落了灰尘的霓虹灯招牌上,无法想象夏天时这里这么热闹。
一个女人从沿海公路上走来。那辆公交车,一年四季穿行于海湾和火车站之间。它在这个季节,照常行驶,每隔十五分钟一趟,从上午六点到下午七点半。女人下车后,向路边看了看,过了公路,就来到了海滩。风呼呼地吹着。虽然我穿得很厚,海风还是轻轻松松地,就把羽绒服打透了,身上的温度,正一点一点下降。几只白色的海鸥掠过,我没有抬头看这些灰头的小家伙。这些鸟真奇怪,飞累了,光着脚,立在海水之中,咕咕叫个没完。对于它们来说,无论男女,人都是外来者。它们的叫声,保持着一个协和又单调的节奏,回荡在小小海湾的上空。每年夏天,这里都人满为患。十月尾声,海湾收起它的热情,转脸就是另一副样子。
她从公交车上走下来,看到了这片黄昏的海滩,也看见远处的礁石上,有一个男人在走动。太远了,也看不清脸。女人背着一个酱紫色的双肩背包,掏出手机,似乎在看导航,然后又沿海滩,继续向前。那个看不清脸的男人,过了一会儿,从礁石上离开了。女人走着,男人很快在海滩上出现了,他们保持差不多的距离一没什么好担心的,现在她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现在,你一定觉得,这个故事要讲的,可能是一个女人去海边了结余生。你可能会幻想她在家里已处理好孩子,她平时没时间照顾孩子。孩子一直想和妈妈安静地躺在一起入睡。离家前夜,女人关掉手机,躺在孩子身边,做最后一次陪伴。
女人在海滩上走了很久之后,看到沿海公路旁一家小旅店开着。她在那里开了一间房,进屋后,从背包里把啤酒和安眠药掏出来,放在木纹色的茶几上。她没有坐下来,而是站到那个面向大海的落地窗前。她拉窗帘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巨大的关门声。不过,那个声音很快被窗外的海潮声遮住了。
天黑以前,女人穿上深灰色的风衣,蹲在沙滩上,点燃了自己带来的照片,照片上,多半有另一个男人一我们没法知道男人的身份。是丈夫?是男友?
只知道她很专注地焚烧着这些已经逝去的和正在逝去的记忆,忽然一个男人跑到她身后:
“对不起,你见过这个人吗?
这个男人从哪来?为什么要问我女人抬头看清了他的脸面容苍白,却有着一双好看的眼睛。那双眼睛在这寒冷的天气里,投来一丝温暖。
“那你,之前来过这吗?
男人趁女人不注意,随手把一沓剧本,丢在火上。火继续燃烧。纸片很快化成了灰烬。
“这……是什么?”
“已经是一堆垃圾了。”
海风吹走了火堆里的灰烬。没过多久,灰烬被吹散得精光。
我在麦当劳坐着时,又遇上了这女人。我們在海边走散后,我就有种还会见面的感觉。这里地方很小。
这时,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对坐麦当劳,总像会发生点什么似的。在他们说话的过程中,男人偶尔离座,去柜台取食物。女人看他离开,又走来,又离开,眼神始终追随着他。他们似乎还谈起了很多关于生活的话题。也许与陌生人的交谈是最安全的一不必担心隐私暴露。男人和女人聊了很多,还提到了明年这时……他们一定要见面,再要干点什么才可以。总之,乐观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初冬时节,小小海湾,入夜街角,只有麦当劳的灯光还亮着。这一点,去年和今年没有什么不同。
去年的这个时候,男人走出麦当劳之后,女人也追了出来。他们就近找了一家小旅馆,暖风空调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把他们缠绵的声音完全掩住了。突然,赤裸的男人伸出手,掐住了女人脖子,女人的表情一直平静,没有露出惊恐,也没有收起陶醉的微笑。
她在高潮中死去了。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窗帘外是一片蔚蓝的海。女人的房间隔壁,响起了一声开门声。茶几上备好的安眠药和啤酒都不见了。
房间里有一个女人,麦当劳里也有一个女人。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寻死而来,现在却想干嘛不好好活着?
那年冬夜的海边,我在旅馆与麦当劳之间的夜路上游荡,像发生了什么事似的。
“外国有个海滩,每年都有很多人临死前去往那里,即使是在冬天。因为那里太冷,好多能忍受住寒冷的人会更慎重地选择一次,那是产生转机的地方。”
而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同时,我在夜路上游荡时,心想,到底如何更具体地描述这个女子,或者说这次奇遇,才对得起这一夜。
三
“长夜"是最后一束阳光到第一束阳光之间的距离,也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时刻,我想起了初吻和最后一个吻之间发生过的很多事。当然,记起来的并不多。生物钟紊乱过的人都有一个同感一分针秒针在身体的某条神经里,你推我攘,沿着不可预知的方向,簇拥而去。这感觉在黎明降临前的那段时间,尤其鲜明,为了让自己熬过黑暗时期,人最好紧闭双眼!先别作任何思考。是啊,要是能按下暂停键的话,人就真是一台机器了。从那天开始,他总是过一会儿,就从床上爬起,夺门而去。他希望找个地方释放掉不好的情绪,于是在楼下找到了一家面馆。
在面馆的几小时,自己是唯一的顾客。面馆内部装修极其简易,陈设也单调,在门口靠左的位置,不知谁拿火炭灰,胡乱地写着“拉面馆”三个字。小县城周边多是这样。这是一个过渡地区。到了吃饭时间,许多口音,会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爆发——现在,什么也听不到。面馆生意由工地工人支撑着,收入应该还可以。他通常在窗前位子坐下来。上来招呼他的老板是一个兰州人,白白胖胖,两撇小胡子。当他每次凌晨走进面馆,老板都送上同样的笑容。微弱的光浮动着,还有几束光,窜上了他疲惫的身体。眼药水也用完,他的眼前一阵恍惚。他的位置旁边有个窗户。窗外的路上,噪音滚动。拉面上桌前,可以想象一下小城里每个熟睡着的陌生人。他们的睡姿,他们白天筋疲力尽地工作,以及他们的枕边人。凌晨之后,这些人就陆续进入他的生活,又在天亮之后从他的生活里逃出去。面条端上来时,一个神态极像他老婆的女子走进来。其实,他老婆的事比失业的事更有预兆。他却不那么认为。他认为,老婆也是带着这种看上去十分陌生的神态,从他的生活中走出去的。失业的故事一点也不重要。那太突然了。公司老板把钱吞了跑路与他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是有关系的,老婆以此为由,不仅自己走了,还带走了女儿。这个走进来女人是陌生人,他却难以抑制想象。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他的内心在说话。女人点了一碗面,看着径直走过去一个人。空桌很多,她却没有离开那张桌子。面条里的辣椒让人满头大汗,鼻涕倾涌,狼狈不堪。像生活中的不幸,总是如此奏效。
在面馆的几小时,相视而坐。她说,知道你会走过来。我见过你,你总坐在这,在这张桌旁。又说,你是我今天看见的第一个人。他看一眼窗玻璃里的自己,尴尬一笑。女人的头发随风飘动,时而挡住他的视线。问题没有换回他的回答,只发觉她居然也有一双他女儿那样的单眼皮。这种单眼皮间荡漾出来的眼神不够夺人,却多出一份合情合理的忧郁。回头想看向柜台后的老板,他人已不在那里,后厨传来笑声。欢乐不在这里。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面条变凉,坨在汤汁中,成为一团一团凝固的生命,而胃却拒绝埋葬它们。这是一首诗吗?白净的脖上系着一条项链。这是他老婆没有的,还有它的吊坠是一种植物——属于他这个不会生活的人无法赋予名字的种类。今天是他生日,他永远不会知道降临人世的那一秒自己在时间紊乱的流逝中想到过什么。一声啼哭把生日逐年逐月推演成一个符号,暗示着方向不明的命运。他的确饿坏了……除长相酷似他老婆以外,女人已经激不起任何联想。
生物钟紊乱的感觉,让两人在铺设中的公路边,望向沿不可预知的方向簇拥而去的陌生人群发呆。淡光散落,手臂、肩膀上的汗毛,在微光下呈现出一种叫不上名字的颜色。他不知下一秒该去何地遇见何人。所以,害怕有花不完的时间,非得逼他把它们耗尽。也是时间把他连拖带拽地,从儿童变成少年,少年变成青年,今后这个定势会将他从青年推向老年,这时分,他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反正,坐在女人对面才是重要的,重要到精神紧张不知怎么应对她的话题。她说起自己痛恨牛肉,每次只吃面条除此之外,好像都是对的。听不出什么破绽。他们认识?他们不认识。他走向她时,其实他知道……对……他不认识她。只能说他们之间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她指着面馆外面,语调缓慢地说,上星期,他和我说,如果我们还能再见……看来,他们并没有再见。女人都是这样为爱而伤。他是谁,已经不再重要。
从阳台上,望向对面褐色的旷野,绕过一圈柏树、刺槐交织的树林,还有树林之外淡淡山峦的痕迹,收回视线时,难免要从路边的面馆扫过。这一眼如花朵盛开,她绽放。她们在绽放的花萼里隐藏着纠结的心绪——她也不是第一次到面馆来。
他们能在面馆倾吐往事,就是因为他们似曾相识。他生长在这里,却从未喜欢过这个漫天灰尘的小城。现在,又必须在这个乏味地方念完大学。然后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
他希望乏味的生活里发生奇迹。待会儿,带你去一个地方。他说。刚才,面馆里又进来一个人,看看,又走了。也就是说,面馆仍然只有两个人。一切就像没有中断过,只是一次恍神。嗯。随便说,不愿意也没关系。他想知道女人的反应。你肯定有过一场爱情?说不定现在还活在其中。他故意这么说。为什么一个人竟可以爱自己老婆之外的另一个?这个女人比他老婆年轻,脸上洋溢着一种独有的光芒。他坐在这里,证明他还有一部分活着。活着好,可以旅游,可以恋爱,可以打架,可以骂人。他觉得自己是个好男人,至少没有爱上老婆之外的另一个,但这没什么意义,老婆还是走了。我们会认为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来同一个地方吃同样一碗面条,是一种反映内心世界的仪式。高楼上的某个房间,此刻灯依然亮着。能不能让我知道,爱是什么?女人的青春让他倍感衰老。他应该在睡梦中死去,无声无息。你和情人接吻吗?除小时候不懂事,他没有跟任何人接过吻,不要误会一我以为,你渴望一个吻。几年前,他设想毕业之后爱上一个人,之后结婚,很快,对,很快,快马加鞭。一个跟她差不多的单眼皮女儿出生。一个人的长大,伴随另一个人的变老死去。时间、地点、人物都与他的这个意愿有关。所有改变都是为更好地忠于开始吃面時的沉静与忧伤,如同随便什么悲伤故事的尾声。
像相遇,她忽然说。到目前为止,他分不清到底发生什么。此刻看着她,这是生物钟紊乱的恩赐透过她的样子,看见自己的老婆。那张年轻漂亮的脸上呈现出一种绝妙的均衡感。开始,他不知为什么,接着他发现那个耳坠——小耳朵妩媚精巧,还有淡蓝色血管在透明的肌肤下闪动。
“我花十年时间来见他,但他可能只用十秒时间判断一下,就可以走出去。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吃面,他也吃面,还有你也来吃面。如果有一杯酒,你该敬我一杯。”
女人说的,明明是另一个人。但“他们”的界限好像越来越模糊。她是讨厌牛肉的面馆客人,这一天的第二个客人。两个可能已经被周围环境忽略的人在此相遇。清晨如梦境,相遇似诀别。
在面馆里,老板打着瞌睡,梦里有他的故乡。他和女人说过想回去,却没有动身的意思。他有个女儿,他也是父亲。他渴望献出一切,在梦中他和老婆相拥而眠。背景是夜空、阴霾、星星、月亮、红色被套或蓝色台灯。他们开始亲热,他们多默契,他们如过去一般体贴,第一次那样富有激情。他们汗水交融,在封闭房间,竭尽全力,挥霍快乐。他将为没有爱上一个人而感谢自己。他拉住她的手,柔软、纤细、潮湿、熟悉、陌生。他抚摸着她的每根手指,他让她的指甲在他的皮肤上狠狠划过,甜蜜侵入神经,响彻全身。他轻拾露珠,融入清晨,他张开双眼,他对面是工地的灯光。
在面馆里,坐着几个民工,他没有感觉到其他客人的注视。终于有声响。新客人来,他也该走了。他吸最后一口烟。面馆门外的汽车喇叭声是一个结束。
她走,他也走。女人在出租车前,拥抱了他。天亮以后,面馆之外,最初的场景是一个人疾步而行。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脚步混杂,人们议论。一个男人站在面馆对面,二十四楼阳台上,慢慢地,滑倒在地。失眠不是最可怕的,等待天亮的感觉,在身体的某条神经里,你推我攘地,沿着不可预知的方向,簇拥而去。黎明即将降临之前,黑夜还没有退去的一刻最为动人。为让自己好熬一些,紧闭双眼吧!再过一会儿,他就该从床上,爬起来了……
四
事发突然。它来自我跟一个老同学的对话。
“现在,老家人生活得都不错。当然,女人比较好过一点,老实巴交地去站超市收收银。不想站着的,又馋又懒的,去卖卖淫。”
说话的人叫小丽,说话大大咧咧,不管不顾。她住在我家左边。她和住在我家右边的小美,还有我,都是老同学。我们小时候住得很近。
小丽和小美从小要好。前段时候,我回老家,见到小丽。她跟我形容她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我在外面混得那么辛苦。生意多么难做,压力多大,她统统不关心。
每次说起生活,她只有一句话:“真他妈的!”
一个叹词和感慨。小时候我们就这么说话,现在我们长大了,倒是有些拘谨。可又想这么说,通常开始不说,吃到一半,外人听到我们吃饭就像打架。我希望一切还能和过去一样,事实上不太可能。后来,我们聊起我们共同的朋友小美,她又是一句:
“真他妈的!”
小丽不如小美学习好,小美职校学会计毕业之后,在村办冰块厂当会计。如果不是在那个特别远的冰块厂当会计,也不会后面的事。
盛夏时节,冰块畅销,厂子在那段时间总是加班。小美回家的路上被人强暴,刚开始时还是一件大事。有人说,下夜班之后,工人都走光了,小美很晚才算完账。她走过厂门口,不远处的厂房,冰凉的气息把她撞了一下,紧接着她打了一个冷战,骑上自行车,走了。天很黑,小美骑着自行车冲入一片树林。那片树林不大,平时走,天都亮着,她现在觉得林子一下被黑夜抻大了。走了半天,小美和她的自行车还在树林里转。后来她就被一个黑影挡住了。下面的事每天都发生
“下来。”
小美下了自行车。
“过来。”
小美打了车梯。
“快点,老子叫你快点。”
她觉得,自己被充血般的疼痛搞得浑身刺痒,一路骑着车,坚持回到家。身上散发着浓浓的汗味,她的手在淋浴下四处梭巡。水流冲过皮肤,不知不觉中,她失去了知觉,疼痛也在那时消失。浴室里的水蒸气越来越大,小美开始不断挥舞手臂,企图驱散覆盖在身上的烟雾。后来,什么东西烫了她一下,她的手则把守住下面,另一只手拿着肥皂,不断摩擦,38.5摄氏度的屋里波涛汹涌,门楣、门框、门槛都发着亮。她有点不知所措地抖动身体。你个浪货!她小声骂自己,一边骂一边哭。回到自己屋子里时,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像小时候第一次看见自己裸体的样子。
原来总是在那里见到她。小丽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树林那片都见不到她了。我每天晚上下班都从故意从那里骑自行车走——其实,我可以从另一条路,我以前都是走另一条路。一条异常开阔的路。夏天,两旁坐满人。即使冬天,那也会有很多卖烤白薯的小贩,塞满每根电线杆间的空隙。那片树林挺小的,在村里边上,我们当年经常从那里走过,去市里办事。我想到这点之后,看了看小丽。小丽有点情绪变化,但不明显。
和很多社会大事一样,众人热议一阵后,它不了了之。再后来,听小丽说,小美好像找了个外县男人过起了日子,本地人都假惺惺的,没人要她,真他妈的!
和很多我们老家的夫妻一样,一生不幸福,不悲惨,就这么彼此无感地活着。总归是活着。
五
暗巷中时而闪出一点亮光。流动的光斑有些神秘。据说那片地方,很快要拆了,旧年头它作为一片烟花之地,留存在那些陆续搬走的人的记忆里。
剩下一批老建筑,现在来了不少年轻人开酒吧和餐馆。一到时间,暗巷中有不少女孩出来吸引异性。警察多次查抄也没效果,后来索性不太管。所以到了天黑后,就有一些身着亮片短裙的女孩,在街边游弋。
四天前某个入夜时分,下过雨,路上偶有积水。这片的路灯,修修坏坏,一直都是隔一段,一片黑。
我和三五好友坐车,正在去那里的一家餐馆吃饭。车冲下立交桥,转入一条大路口,就拐进了暗巷,越往深处去越黑。路边的霓虹灯,照不亮前方,只有门口积水的地方,流光溢彩。
我们的车一头扎进暗巷。里面有很多苍蝇馆,平时开车来的人也很多。燈光就在街上交织起来,偶尔异常亮。
我指了指车窗外。
一个紫色头发的高个女孩,从一个发廊里跑出来,往路边的垃圾桶里,吐了一口什么。为大家开车的姑娘,瞥了一眼窗外,嚼着口香糖,又说了一遍:
“男人挺变态的!”
身后有人超车,开车的女人打了一下方向,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们说话。
忽然,对面车灯晃了一下,眼前一片空白,“砰”一声响后,女人一脚刹车。
“是不是撞到什么了?
车停在路边,两个路灯之间,让出了一条车道。我从后窗,探出头去,看了看。半天才看清远处路上,一团灰色的东西还在动。车上的人,互相看看,开门,纷纷下车。
虽然有一个路灯,可距离有点远。灯光照不到那块地方。我们走到那,看清躺在地上抽搐的是一条柴狗,个头不小,肚子上裂开一道口子,花花绿绿的肠子撒了一地。它的头还剩下半个,爪子上都是血,一只眼睛瞪着我们,舌头从嘴里耷拉出来,斜斜地,使劲想去舔地上的血。它的嘴一直在抖动,伴有唧唧的声音。不过街上车声隆隆,不细听,听不清。
“看样子,马上就要死了。”
“可它在动啊,送宠物医院吧。”
我看了看四周,有车开了过来。
“你说呢?
“没那个必要,都这样了,活不了了。”大家站了一会儿,陆续返回车内。谁也没听女人的建议,没有一个人去碰那条受伤的狗。车离开时,它依然躺在原处。很快就会有别的车,疾驰而过,它的痛苦不会持续太久。
这么做是最好的。刚才开车的女人坐到后排,另一个人去开车。我一直扭着头看。“有什么好看的?
刚才街边那个吐什么东西的女孩,走到了那块灯光照不到的那边。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她在一个卖炒饼的小摊上停下来。小摊边,围着很多夜行人。
汽车启动后,车窗外飞扑过来模模糊糊的景物,我不禁想象,假如躺在地上的是一个人呢?我不是没想过救它,稳妥的办法是把它弄到街边,找一块砖头彻底解决。一块不够,就多搬几块,朋友几个围成一圈,轮流帮它解决,像是一个行刑队那样。我们的目的听上去很高尚--为了结束痛苦。
夜色更浓了。我们坐在那家餐馆靠西的个方桌旁。桌子正对门口,因为是夏天,这里比较凉爽。餐馆的老式吊扇吱吱呀呀地转半天,并不管什么用。老板在我们用餐时放了点音乐。
“对,”我们中的一人说,“太好了,一定要来点欢快的音乐。”
“刚才的事,让它过去吧!”
坐我对面的女人,叹了一口气。
“它自己突然窜出来的……那么黑谁也看不见。”
真的,我在车上的沉默,不是想责怪谁,只是不知道说什么。
“咱们怎么也这么冷漠了?
真的,只是不知道说什么。
“变态的冷漠!”她补充完自己的意思,端酒一饮而下。
刚才说话时,她一直看我。而我似乎意识到当时下车后,自己不该提什么送医院。周围几个人,面面相觑。
生活中这种小意外,处处都是。它发生了,正确的处理办法是当作没发生。不晓得今天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冲动,突然想那条狗还活着。怎么能看着它死?一定要去把它弄到街边,至少不会再被别的车轧到..辵来这个冲动,让我变得坐立不安,神情恍惚。迷迷糊糊之中,好像看到了一个背影,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向了那条街,那个路灯照不到的角落。
唐棣,导演、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西瓜长在天边》《遗闻集》等。
猜你喜欢 面馆 无尽遐想等小读者之友(2020年9期)2020-10-09多赚两只蛋的钱文萃报·周二版(2020年13期)2020-04-14多赚两颗蛋的钱恋爱婚姻家庭·青春(2018年12期)2018-12-13洗肉面馆爱你·健康读本(2018年4期)2018-05-14加什么故事会(2018年4期)2018-03-01灯光海外文摘·文学版(2018年2期)2018-02-21洗肉面馆故事会(2018年2期)2018-01-18面馆兴衰记作文周刊(高考版)(2016年7期)2016-08-12面馆惊魂兴趣英语(2013年2期)2013-04-25